
楚帛書《時日》篇中的天文學問題
作者:武家璧 發布時間:2010-09-13 09:41:25(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
(首發)
目 次
1.四神時代與“天動”模式
(1)四神時代與“四時曆”
(2)反映地球公轉的“天動”模式
2.共工時代與“日行”模式
(1)“千有百歲”反映的曆法問題
(2)“日月”產生與“十日曆”
(3)穩定性問題與奠三天、四極
(4)反映地球公轉的“日行”模式
3.後共工時代與“天轉”模式
(1)共工時代的推步困難
(2)反映地球自轉的“天轉”模式
(3)“逆日月以轉”與“右旋”說
(4)後共工時代與“晝夜消息”
4.餘論
【提 要】楚帛書《時日》篇把時間的起源分成“四時—日月—晝夜”的形成三個時期。第一時期為四神時代,推步“四時”曆,以“天動”機制解釋四季成因。此時沒有日月和晝夜,黃極圍繞赤極“旁動”,帶動黃道天區高低“騰轉”,以生“四時”。第二時期為共工時代,推步“十日”曆,以“日行”機制解釋四季成因。此時“天動”被制止,代之以“日月行”,沒有晝夜,太陽在靜止的天即恒星背景上運行,以生“四時”。“天動”和“日行”兩種模式都是地球公轉的反映,均能解釋四季交替。第三時期為後共工時代,以“天轉”機制解釋晝夜成因。此時上帝啟動天“逆日月以轉”,以生晝夜,依據晝夜消息可解釋四季成因。此“天轉”模式即後世所謂“右旋說”——天左轉,日月五星右行。
【關鍵詞】楚帛書 時日 天文學 地球公轉 地球自轉
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墓出土帛書,由中部八行、十三行及四周三部分組成,一般習慣上按內容稱八行文為《四時》、十三行文為《天象》、四周為《月令》三篇。其中《四時》篇主要講“四時”、“日月”和“晝夜”的起源,反映早期古史觀和宇宙論,是研究上古神話傳說和先秦哲學以及早期天文學思想的重要資料。其中涉及天文學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物理圖像,茲以饒宗頤[1]、李零[2]等先生的釋文為基礎,對有關的天文學問題,略加闡釋,以期對古史及科學史研究有所幫助。
宇宙分為時間和空間兩個部分,中國早期宇宙起源論也相應地分為兩個部分,關於宇宙空間的起源,筆者有過相關的討論[3],這里根據楚帛書的記載探討早期宇宙論中關於時間起源的部分。依據《四時》篇的內容,可把時間起源分成“四時”形成、“日月”出現和“晝夜”產生三個時期。篇名《四時》是今人所加,並不恰當,筆者擬名《時日》篇可能更加切合內容的實際——擬名中的“時”指“四時”(四季)之時,“日”既指“十日”之日,也指晝夜之日,使篇名涵蓋三個時期。
前兩個時期可稱為四神時代和共工時代,四神推步“四時”曆,共工推步“十日”曆,分別以“天動”和“日行”的物理機制解釋四季成因。“天動”階段沒有日月和晝夜,只有黃極“旁動”與黃道“騰轉”,以生四季。“日行”是日月產生以後、晝夜形成以前,太陽在靜止的恒星背景上運行,因而產生四季交替。“天動”和“日行”兩種模式都等效於地球的公轉效應。第三時期為後共工時代,因前期共工推步,搞亂日月五星秩序,上帝乃使天轉而生晝夜,使秩序恢復正常。其科學內涵實即以“天轉”機制解釋晝夜起源,以晝夜消息解釋四季成因等。詳論如下。
1.四神時代與“天動”模式
(1)四神時代與“四時曆”
《時日》篇開篇講包戲(伏羲)娶某氏之子女皇(媧),生子四人。此四子疏通山陵,跋山涉水,以量天測地,被封為四神,負責推步四時。其文云:
是生子四,□□是襄,天踐是格,參化法地,為禹為萬,以司堵(土)襄(壤),咎天步途。乃上下騰轉,山陵不疏。乃命山川四海,熱氣寒氣,以為其疏,以涉山陵,瀧泔淵澫。未有日月,四神相戈,乃步以為歲,是惟四時。
帛文大抵四字成句,頗規整。“參化法地”後二字饒宗頤釋“法逃”,李零釋“廢逃”,按上下文意似應為“法地”。《易·系辭》“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上文“天踐是格”是“效天”,下文當為“法地”,与接下来的“以司土壤”相衔接。
“上下騰轉”後二字李零釋“朕斷”非是,饒公釋“騰轉”甚確。“騰轉”就是輾轉騰挪,是一種全方位轉動,包括水平位置的輾轉和上下位置的騰挪。因“騰轉”必定引起上下位置的高低變化,故稱“上下騰轉”。完整的句式應說“天乃上下騰轉”,並非指上天、下地互相轉動,因為帛書討論“四時”起源的狀況,設想沒有晝夜,甚至沒有日月之時的原始簡單模型,不可能設想有“地動”的複雜情形。因此“上下騰轉”應指黃道天區高低“騰轉”,與下文“天旁動”同義(參見圖1,說詳下)。
按文意天地本應疏通,上下通氣,其連接處就在“山陵”。但由於“上下騰轉”使得“山陵不疏”。這里隱含的物理圖像是說“同氣相求”,九天的寒熱是分區的,只有和地上的寒熱對應才能上下通氣,但天旁轉,天地之氣的對應就切斷了。寒熱之氣阻在山陵之間,四子不能跋涉山水,以完成天文大地測量,於是上帝“乃命山川四海,熱氣寒氣,以為其疏”。四子的測量工作與《堯典》的記載類似,《堯典》載四子之名為“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別被派到遙遠的四方去觀測四季天象。
“四神相戈”與文獻中的“二子相戈”類似。《左傳·昭公元年》載:“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後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為晉星。”辰星西名天蠍座(Scorpio),參星西名獵戶座(Orion),二者相去約180o,在天空中此起則彼落,故俗語云“參商不相見”。帛書解決“四神相戈”的辦法是步天四時以為歲,即將天分為四區,“四神”各相去90o而守一方,一歲之內輪流執掌一季之事,為一時之主,其餘三季各自休息。因此“四神”既是季節神,又是方位神。
四神的“步天”之法,類似《堯典》所載“日短星昴”、“日永星火”、“日中星鳥”、“宵中星虛”等,只是沒有晝夜長短作參考。須確定一個起點(如冬至點),然後直接用勾矩在星空中劃出每隔90o的星區,然後根據某區的星宿開始成為“中星”,即可決定哪位時神當值。四神步天推得的曆法,沒有晝夜和日月,只有四時,我們姑且稱之為“四時曆”。
(2)反映地球公轉的“天動”模式
“四神”推步“四時”只是一種表像,四季的形成有其物理機制。據帛書所載,從物理圖像來看,“天動”是造成“四時”交替的主要原因。先從關於“九天”的劃分說起。《呂氏春秋·有始覽》、《淮南子·天文訓》、《太玄·太玄數》均載“天有九野”之說,《淮南子》最詳:
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
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
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
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
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
西方曰顥天,其星胃、昴、畢;
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參、東井;
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
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
文獻中的“日冬至牽牛,夏至東井”分別位於東北和北方、西南和南方的交界處,實為進入“玄天”和“炎天”的標誌。從“九天”的名字可以看出每一天區的寒熱屬性是固定的,如南方曰“炎天”,依現代的經驗來看,當“炎天”這一天區正午到達天頂時,正是炎熱的夏天;東方曰“蒼天”,當“蒼天”正午到達天頂時,就是蒼涼的春天等等。
帛書設想四神“步以為歲”之後“千有百歲”,日月才產生,則四神時代是沒有日月和晝夜的時代,到處可見星空,判斷那一片天區到達天頂是很容易的。四神“步天”是為了分出“四時”(四季),因此想像中的星空移動只能是周年運動,即“天動”的速度很慢,一年轉一圈,實即地球公轉以生四季的一種曲折反映。
如果九天圍繞同一個中心旋轉,雖然每個天區都會相繼到達人們所在的天頂,但不會形成四季變化。寒暑變化真正的物理機制,並非如古人理解是某天區具有寒熱屬性的結果,而是由太陽帶來的,因為某天區正午到達天頂時,太陽也同時達到。“九野”不過是對“日月之舍”二十八宿的等分而已,與八方的對應大概是人們根據其寒熱屬性人為規定的,其“中央”天區並不在八方的中心位置,顯然為湊數而設。太陽每年週期性地回到某天區,使人們誤以為該天區具備固有的寒熱屬性,實際上是太陽的直射和斜射伴隨不同的寒熱屬性。如果太陽圍繞天極(赤極或北極)轉,就不會有直射和斜射的問題,也就不會有寒暑變化。但太陽實際在黃道上運行,圍繞黃極旋轉,黃道與赤道有一個交角(今值23.5o,古稱24度),因此黃極與北極之間有一個同樣大小的張角。赤極(北極)不動,黃極圍繞北極轉動,使得黃道在天空中的位置,不僅前後左右輾轉,而且上下高低騰挪。黃道位置在高低變化,於是就產生了太陽的直射和斜射問題。在討論起源問題時,人們剝離了太陽的存在,把相關屬性賦予了黃道附近的相應天區,這是可以理解的。
從上面的物理機制分析,帛書所謂“上下騰轉”,實即黃極所在的天軸圍繞北極搖動,搖擺幅度的大小等於黃赤交角(24度),它的客觀效果是可推步“四時”,因此不是周日運動而是周年運動。黃極圍繞赤極的周年運動,是地球圍繞太陽公轉的反映,地球自轉軸和公轉軸的夾角等於黃赤交角。值得注意的是,帛書中的“天動”生四時模式,是想像“未有日月”之前的狀況,即徹底排除太陽的存在,完全超出直觀之外,推測起源狀態的圖景,居然能合理解釋四季成因,其想像力、抽象思維和理論思考能力令人十分吃驚。
2.共工時代與“日行”模式
(1)“千有百歲”反映的曆法問題
帛書云“千有百歲,日月夋生”。“日月”誕生標誌進入新的時代,“四神”獨斷的時代僅“千有百歲”,按文獻當為“千五百二十歲”。首先這個數被認為是五德終始之數,《後漢書·郎顗傳》引孔子曰“三百載斗曆改憲”,《易乾鑿度》引“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備凡千五百二十歲,太終复初’。”《春秋命曆序》說“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千五百二十歲”。
其次,這個數是四分曆“章蔀紀元”結構中的一紀之歲,《淮南子》稱“大終”,《周髀算經》稱“遂”,後漢《四分曆》稱“紀”。《淮南子·天文訓》:“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名曰一紀,天一凡二十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日月星辰复始甲寅之元。”《周髀算經》卷下之三:“日月之法,十九歲為一章,四章為一蔀七十六歲,二十蔀為一遂,遂千五百二十歲。”《論衡·譋時篇》“周髀算經、乾鑿度、淮南天文訓並以千五百二十歲為一統,四千五百六十歲為元。”《續漢書·律曆志》“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复謂之元。…元法四千五百六十,紀法千五百二十…蔀法七十六…章法十九。”
以上名稱雖異,實質相同,我們統一使用《四分曆》名稱。自蔀首76年後再次重演“至朔同日”同時發生在“日始”時刻,前後兩蔀內氣、朔、閏分佈完全相同,但蔀首日名不同。一紀之後所有蔀名恢復相同,稱為甲子蔀、癸卯蔀、壬午蔀等共20蔀。紀首年名有三個,稱為天紀、地紀、人紀。三紀為一元,一元复始,年名、日名恢復相同。
按帛書結構,分為四神、共工和後共工時代,相當於四分曆的天、地、人三紀,故曰“千有百歲,日月夋生”。也有把“紀”稱為“統”者,有天、地、人“三統”之說,《〈周本紀〉正義》“按‘三正’,三統也,周以建子為天統,殷以建丑為地統,夏以建寅為人統也”。人紀或人統在共工之後,應相當於堯舜禹時期。文獻稱《夏曆》為“人正”,《淮南子·天文訓》称“禹以為朝晝昏夜”,故进入“人紀”才有晝夜之分。《夏曆》繼承唐堯虞舜曆法而來,唐虞夏之間以禪讓著稱,沒有發生革命和改正曆朔事件,故唐虞曆法也是“人正”,可歸入共工之後的“人紀”之內。《堯典》記載羲和氏能依據“日中”、“宵中”、“日永”、“日短”分出四季,這與楚帛書描寫後共工時代“有宵、有朝、有晝、有夕”是相符合的。
今知尧舜禹距今约4000餘年,則共工時代距今約5500~4000餘年,四神時代距今約7000~5500餘年。四神相當於考古學文化新石期時代中期的“仰韶時代”,共工相當於新石期時代晚期的“龍山時代”。
“千有百歲”說明帛書實際使用四分曆概念推演起源狀況。四分曆規定1太陽年(回歸年)長365又1/4日,因年長日數餘分的分母為四,故稱“四分曆”。《漢書·律曆志》載“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曆。”《續漢書·律曆志》載有古六曆的曆元年名,《開元占經》載有古六曆的上元積年。因“古之六術,並同四分”(《宋書·律曆志》),為與後漢《四分曆》相區分,一般將先秦六曆稱“古四分曆”。
古六曆之間的明顯區別是建正不同,孔子《尚書大傳》“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為正。夏以十三月為正…殷以十二月為正…周以十一月為正。”《春秋公羊傳解詁》隱公元年:“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殷以斗建丑之月為正…周以斗建子之月為正。”《春秋·元命苞》曰“周人以十一月為正,殷人以十二月為正,夏人以十三月為正。”《〈曆書〉索隱》按“及顓頊、夏禹亦以建寅為正,唯黃帝及殷、周、魯並建子為正(按:一說殷以建丑為正),而秦正建亥,漢初因之。”
古六曆產生于“五伯之末”,是中國推步曆法形成初期。楚帛書抄寫于戰國中晚期,其中天文曆法知識形成的時代更早,估計不晚於春秋戰國之際的百家爭鳴時代,這是一個知識暴漲的時代,與推步曆法形成的時代相合。帛書描寫的推步三時代,反映推步曆形成初期有關天文曆法知識的狀況。楚人是顓頊帝和重黎氏的後裔(《楚世家》),屈原《離騷》自稱“帝高陽(顓頊)之苗裔”,其曆法屬於顓頊曆系統無疑。帛書四周的《月令》篇載有月名與《爾雅·釋天》“始陬終塗”月名一致[4],屬於寅正曆,故帛書寅正曆是《顓頊曆》。夏曆源於顓頊曆,如《新唐書·曆志》云“本其所由生,命曰《顓頊》,其實《夏曆》也。”傳世《夏曆》實即《夏小正》,故帛書《顓頊曆》應屬《顓頊小正》。
(2)“日月”產生與“十日曆”
“日月”產生後出現新的問題。首先是大地的平坦性問題。《淮南子·天文訓》載:“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大地傾斜,將帶來嚴重問題,帛書云:
千有百歲,日月夋生。九州不平,山陵備側,四神乃乍(作),至於復。
“山陵備側”末字從李學勤先生釋為“側”[5],傾側之意。“九州不平”影響日月之行,這個問題有科學內涵,不只是神話問題。《淮南子·天文訓》:“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穀之浦,行九州七舍…禹以為朝晝昏夜。”高誘注“自暘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為九州七舍也。”錢塘補注“王充所說十六道,與此十六所合”[6]。《論衡·說日》篇“日行有近遠,晝夜有長短也。夫复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至十一月,月減一分…歲日行天十六道也。”這種把一天分為十六等分來計算晝夜長短的方法,見於雲夢秦簡《日書》中的“日夕分”表,據分析它不是赤道系統的時間數據,而是地平系統的方位角數據,所謂的“日夕分”都是太陽的地平經差[7]。這給我們一個很強的信息,即帛書“九州”是度量太陽方位的蓋天說地平系統,如果“九州不平”,將影響地平經差的測量。
“日月夋生”,《山海經·大荒南經》云“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與前文所引“二子”、“四神”相戈一樣,如果勢力範圍劃分不當“十日”也會“日尋干戈”,如《莊子·天運》言“日月其爭於所乎”。解決辦法同前一樣,將大地平均分為“十方”,“十日”各守一方。前者只須二等分、再二等分圓周即可,而“十方大地”涉及五等分圓周的問題,這是個數學問題,先秦時已能解決,這里不加討論。問題是“九州不平”,十等分地平圈就不會均勻。古代一般用長度單位度量角度,如描述兩天體之間相距1°稱“差一尺”等[8],那麼等分地平方位最好要求大地平坦。實際情況是人們經常看到太陽“出山”,這樣的地理環境人們無法改變;但如果山勢較平,問題也不大。然而帛書描述的情況很嚴重,就是“山陵備側”——所有的山都是傾斜的。所以“四神”的首要任務就是“至於復”——使山陵恢復原來的地勢。如果說上次疏通山陵是“四子”借助上帝神力所為,此次覆平山陵,就是“四神”親力親為了。
大地覆平了,“十日”安頓下來,反映在曆法上,就是把一年分為“十日”,每“日”36天,我們姑且稱之為“十日曆”。在我國西南少數民族彝族、僳僳族、白族、土家族中盛行一種叫“十月曆”的太陽曆[9],一年十月,每月36天,加過年五、六天,等於一太陽(回歸)年。“十月曆”的發現,證明這種太陽曆在原始先民部族中確曾出現過,彝族“十月曆”等很可能就是上古共工“十日曆”的孑遺。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帛書講起源時期的“日”和後來習慣上的日(晝夜)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一年的十分之一,按文獻記載可稱為“之日”。如《詩經·豳風·七月》云: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
二之日鑿冰衝衝,三之日納于淩陰;
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禮記·月令》載“季冬之月…冰方盛…命取冰”;“仲春之月…天子乃獻羔開冰。”從上引文字推知“一之日”必在仲冬(冬至月);“二之日”到“四之日”等於季冬到仲春,三個“之日”之間相差三個多月,每“日”應是36天,故“十日曆”或可稱為“之日曆”。把“鑿冰”和“開冰”,直接與“之日”相聯繫,不與“月”聯繫,是因為“日”與“冰”有直接關係,而與“月”沒關係,因此是一種純陽曆的安排。
按上古的神話系統,在正常情況下“十日”不能並出,只能由飛鳥馱一日出行,其它九日藏在各自的“日舍”裏,等待出行的太陽來臨就取而代之。如:甲日運行到乙舍,乙日取而代之;乙日運行到丙舍,丙日取而代之;如此等等,往復無窮。“十日”的位置是輪換的,每“日”的太陽不同,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禮記·大學》)。由於沒有晝夜,日出和日止在同一地點,故“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山海經·大荒東經》)。這樣的“日舍”按理應在天上的二十八宿之中。
(3)穩定性問題與奠三天、四極
日月產生後,必須解決“天動”模式遺留下來的穩定性問題,以使日行有一個穩定的通道,或者說以“日行”機制取代“天動”模型,以解決四季的形成問題。“天動”模式與傳統宇宙結構形成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就是對“擎天柱”產生摩擦,使之隨時有折斷的可能。如前所述“四神”處理了一次天柱折斷問題,使九州覆平,難保同樣問題不會再度發生。帛書云:
天旁動,攼畀之青木、赤木、黃木、白木、墨(黑)木之楨。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思郛,奠四極,曰:“非九天則大側,則毋敢蔑天靈(命)。”帝夋乃為日月之行。
“天旁動”諸家釋“旁”通“方”,非是。“旁動”就是“旁轉”,古代天文專指一種繞轉方式(圖1),如《晉書·天文志上》:“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顯然“旁轉”是對日月之行的“黃道”而言的。中國古代雖然沒有明確的“黃極”概念,然此“旁轉”實指黃極圍繞赤極向右(東)轉,帶動黃道跟着騰挪轉圈。
如果“天動”是繞軸自轉,摩擦均勻,天柱還可以適應,但天卻是在“旁動”、“騰轉”,即搖晃着打轉,天幕忽高忽低,“擎天柱”就很危險了。帛文“墨木之楨”末字從李零釋“楨”,《爾雅》“楨,幹也”。“扞畀”諸家以“扞蔽”解之。今案《說文》“扞,忮也”,段注“忮當作枝。”則“扞畀”乃“枝蔽”之意,是謂五木以枝遮蔽主幹。帛書四角繪有青木、赤木、黑木以及墨線白描的白木,皆作主幹粗壯而枝繁葉茂狀,其枝葉應是用來捍衛主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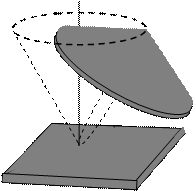
圖1 “天旁動”示意圖
五木自蔽畢竟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最根本的方法是制止“天動”。這只有上帝才能做到。作為上帝的“炎帝”乃命楚人的祖先祝融啟動兩個神系統來制動,一個是作為“四維”神的“四神”來“奠三天”;另一個是作為“四方”神的“□思”神來“奠四極”。
奠定“三天”“四極”是為日行作準備,它們應該在二十八宿的“九野”分區上。“三天”在四維上應是西北幽天、東南陽天、中央鈞天。“四極”如《周髀算經》卷下之一載:
凡日月運行四極之道……故日運行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凡此四方者,天地四極四和。
此謂太陽運行到某極,對沖兩極之間的晝夜正好相反,這在東西方向是正確的,在南北方向應是寒暑相反。帛書討論的是未有晝夜以前的情況,但四極的位置應該沒錯,具體位置如《漢書·天文志》所載:“(日)北至東井…南至牽牛…冬至角,西至婁。”冬至點在“牽牛初度”的年代約在公元前450年[10],楚帛書抄寫年代在戰國中晚期,故其所奠“四極”就是上所列的二分二至點,在天的四正方向上。
(4)反映地球公轉的“日行”模式
“天動”被四維、四方神制止以後,“四時”產生的原有機制沒有了,怎麼辦?於是“帝夋乃為日月之行”,以新的機制取而代之。這里的“日行”是天靜止後太陽在恒星背景上的運行,因此是周年運動。太陽的周年視運動是地球圍繞太陽公轉的反映,這是顯而易見的。
關於“日行”與“四時”的關係,文獻多以“日行遠近”來解釋。《呂氏春秋·有始覽》“冬至日行遠道…夏至日行近道”。《論衡·說日》“夏時日在東井,冬時日在牽牛;牽牛去極遠,故日道短;東井近極,故日道長。…故曰日行有近遠,晝夜有長短也”。此處“日道”指太陽周日視運動圓周上的晝弧,相應的夜弧稱“夜道”。這里解釋白晝(日道)長短與日去極遠近有關。《周髀算經》載日行“七衡六間”以生二十四節氣,“七衡”指以北極為中心的七個同心圓(衡),分佈在周天傘蓋上,“日冬至在牽牛,極外衡…日夏至在東井,極內衡”。以上是蓋天說的解釋,以太陽周日視運動的晝弧(日道)的長短,來標誌日行去極遠近,進而說明四季成因。因為太陽去極遠近是肉眼很難判斷的,而晝夜長短可通過計時工具測知,故可通過晝夜長短依據蓋天說的“七衡圖”推知日行遠近。帛書在這裏所說的是有“日行”之後、無晝夜以前的情形,既無晝夜,則蓋天說理論完全不適用。
渾天說的解釋如《漢書·天文志》載:“黃道…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日)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所謂“日南北”就是去極度,此處用晷影長短來標誌黃道日行去極遠近。太陽在恒星背景上的位置,除了日食以外肉眼是看不到的,古人一般利用晨見昏伏星、昏旦中星或者夜半中星來推斷太陽在東西方向上的位置,如果只需要知道太陽的南北位置,可通過晷影長度測得去極度的遠近。
“晷影”一般指立杆所測正午時太陽的影長,它是正午太陽高度的直接反映。太陽高度是其天頂距的餘角,而天頂的極距是北極高度(地理緯度)的餘角,顯然太陽去極度等於太陽天頂距加天頂極距,故太陽去極度等於太陽高度的餘角加上地理緯度的餘角。晷影長短實際上是由太陽的直射和斜射引起的,故用晷影與去極度相聯繫,以解釋冬夏至和四季的形成,更具有科學性。在未生晝夜以前,我們將“晷影”測量推廣到任意時刻的太陽高度,那麼不需要引入“晝夜”概念即可說明四季的成因。以上分析可以用來說明帛書“日月之行”以生四時的理論。
渾天說與蓋天說最大的不同是引入“黃道去極度”的概念,《隋書·天文志》逕稱為“渾天黃道去極”,又載“祖暅為《漏經》,皆依渾天黃道日行去極遠近,為用箭日率”。“黃道去極度”即今“太陽極距”或“太陽去極度”,如上所述它可由正午時的太陽高度得到,它同時又是是太陽赤緯的餘角(當去極度大於90o時等於90o加赤緯的絕對值),在現代天文學中太陽赤緯是季節的決定因素。最早把“黃道去極度”引入曆法的是《夏曆》。《續漢書·律曆志》載“《夏曆》漏刻隨日南北為長短,密近於官漏……以晷景為刻,少所違失,密近有驗。”這里的“日南北”就是太陽去極度。劉昭注引張衡《渾儀》曰“今此春分去極九十少,秋分去極九十一少者,就《夏曆》‘景去極’之法以為率也。”《續漢志》中華書局標點本《校勘記》按:“‘夏曆景’,影印宋本《御覽》引作‘夏曆晷景’”,故上引《夏曆》“景去極”之法,應是“晷景去極”之法。這里證明《夏曆》有獨具特色的“晷景去極”法。
《史記·曆書》載“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算轉曆,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索隱》引陳壽《益都耆舊傳》“閎…隱于落下,武帝征待詔太史,於地中(洛陽)轉渾天,改《顓頊曆》作《太初曆》。”落下閎參照《夏曆》的“日辰之度”作為《太初曆》的標準,這表明《夏曆》有不同於其它諸曆的曆法數據,並且在漢武帝以前就已存在,這不大可能為秦及漢初時期所草創,應屬於先秦古曆,即孔子主張“行夏之時”所依據的《夏曆》。以上分析表明先秦古六曆中的《夏曆》使用了渾天說理論的“晷景去極”之法,與帛書的時代相合,故可用於對帛書的解釋。
帛書的時間起源說,使用了類似于現代科學理論的“假說”方法,排除次要因素,解釋主要成因。假設天球(或天蓋)靜止不動,只考慮“日行”黃道,解釋四季成因。根據《夏曆》的“晷景去極”之法,只要有“日行”,自然會有“去極度”變化,引起晷影長度變化,晷影長則太陽斜射,晷影短則太陽接近直射,寒暑四季就形成了。不過這里的“晷影”不是每日中午時太陽的影長,因為帛書起源論假設此時還沒有晝夜,那麼日行一周天為一年,實際上一年只有一個晝夜:春分日出,秋分日落;夏半年為白天,冬半年為黑夜;黑夜無晷影,日出入時的晷影無限長。
此時“日出—經天—日入”的路線並非如平時所見為平行於赤道的緯圈,而是與赤道相交24度的大圓——黃道。太陽位置本應由黃道二十八宿來表示,但由於沒有夜空,人們看不到恒星,只能對準天頂將太陽位置投影到地平方位上,因此單純根據“日行”制訂的“十日曆”只能是地平曆。從下文可知“日行”方向與產生晝夜的“天轉”方向相逆反,故“日行”為西升東落。設想“天動”停止、“天轉”未生,沒有晝夜、只有“日行”的情況——就是一年一次的“太陽從西邊出來”。
帛書起源說的“日行”機制比“天動”機制,解釋四季成因更合理、更直觀,它揭示了太陽是寒熱變化的能量來源,太陽直射和斜射是四季形成的根本原因。先秦兩漢時,另有“地動說”,包括地有“四遊”“升降”說和“天旋地轉”說等,以解釋四季的成因[11],雖然後者更接近物理真實,但帛書的“日行”說代表主流說法,也是最簡潔明晰的理論。
3.後共工時代與“天轉”模式
(1)共工時代的推步困難
前文所說“四時”“十日”都是陽曆因素,如果沒有“月”的參與,不會有陰曆因素。單純的陽曆推步在“四神”時代比較簡單,那時不僅沒有晝夜,也沒有日月,隨時隨處所見都是星空,故推步“四時”就是步天中星。出現日月之後、沒有晝夜之前的曆法推步顯得比較混亂。帛書云:
共攻(工)誇步十日四時,□□神則閏,四□毋息。百神風雨,晨禕亂作。乃逆日月以轉,相□息,有宵有朝,有晝有夕。
帛文“四□毋息”與“相□息”中的末字本作“思”,從李零釋與“息”通。“乃逆日月以轉”的“逆”字從饒公釋。
共工推步的曆法就是“十日曆”或“之日曆”,須與四神推步的“四時曆”相協調,故帛文說共工“步十日四時”。共工推步比四神推步最大的不同,就是出現了日月卻沒有夜晚,星空完全消失。太陽位置沒有恒星背景無法描述,只有把太陽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引申到地平圈上,通過地平方位來表示,地平上的“九州七舍”(十六分)就是這樣的系統。共工推步遇到的第一個難題是,太陽在地平上轉過相同的角度,經過的時間不等。從現代天文學知識來說,就是地平坐標系與時角坐標系不同,太陽方位角不等於時角,赤道上的二十八宿距度不能按比例化為地平經差,兩者是三角函數關係,沒有簡單的比例關係。依據地平系統,共工推不出相等的“日”的長度。
共工推步的第二個難題是,用“十日”把一年平均分為十等份,“十日”和“四時”沒有公約數。“四時”代表一回歸年,約365.25天,平均分為十份,每份得整數36天,十份共360天,比回歸年少5.25天。彝族“十月曆”把剩餘的五至六天作為“過年日”[12],共工曆因為不考慮日(晝夜)的存在,怎樣計算閏餘不得而知,但累積若干年設置“閏日”是肯定的,故帛書有“神則閏”字樣。
共工推步的第三個問題,可能是個神話問題,具體情況不明,依據帛文“四□毋息”推測是與四神推步發生矛盾,或得不到準確的“四時”,致使本已平息干戈的“四神”又起衝突。在曆法上的後果就是“晨禕亂作”,“晨禕”應作“辰緯”,分別指“日月之辰”和“五緯”。按照共工的推步,不該發生的發生了,該發生的沒有發生,就是“辰緯亂作”,即日月合朔和五星位置發生錯亂。
(2)反映地球自轉的“天轉”模式
帛文“乃逆日月以轉”是指上帝啟動了“天轉”。這次“天轉”與四神時代的“天動”有本質區別。首先,前次的“上下騰轉”和“天旁動”是整個天軸在搖動,從而帶動所有天區騰挪而變換黃道的高低位置;此次“天轉”的天軸在原地不動,是一種繞軸運動。其次,前者產生“四時”,是周年運動,故搖動的速度很慢;後者產生晝夜,是周日運動,故繞轉的速度很快。再次,從兩者相對於日行的方向來看,它們轉動的方向相反。
先看日行的方向。考慮兩種球面方向:一種把地球放到球心,太陽放在球面;另一種正好相反。在地心天球上,太陽從冬至點移動到春分點,等效於在日心天球上,地球從夏至點移動到秋分點,從直線方向來看,兩者在每一瞬間都是相反的。設想太陽和地球兩者位於同一個天球上,在各自的對立面(相差180o),那麼平面相反的方向就變成球面一致的方向了[13]。因此我們看到太陽在恒星背景上自西向東行進,那麼這個方向正好是地球公轉的方向,與地球自轉的方向一致。我們知道四季形成是由地球公轉也就是太陽東行造成的,帛書推斷在沒有太陽以前就已形成四季,那就只有設想天球(或天蓋)自西向東轉來取代太陽自西向東行,才能達到同樣效果。據此判斷四神時代的“天動”是自西向東的。而自共工以後的“天轉”是“逆日月”方向的,因而是自東向西的。古人判斷天西轉,是根據恒星東升西落的周日視運動作出的直觀判斷,實際上是地球自西向東自轉的逆反映。
(3)“逆日月以轉”與“右旋”說
天球或天蓋“逆日月以轉”,是“天轉”和“日行”兩種運動的复合運動,實質是地球公轉和自轉的綜合反映。習慣上判斷天轉或者星行的方向,是面對北極而言的,由西向東等於由左向右轉,稱為“右旋”;由東向西等於由右向左轉,稱為“左旋”。古人認為恒星附着在天上,漫天星斗東升西落,表明天“左轉”,這一點自西方天文學傳入以前,中國古代並無異詞。有爭議的是日月五星的運行方向,分為“左旋”說和“右旋”說[14]。
“左旋”說以《夏曆》為代表,《宋書·天文志》引“劉向《五紀》說,《夏曆》以為列宿日月皆西移,列宿疾而日次之,月最遲。”緯書《春秋元命苞》曰“日月左行”。《太平御覽》卷二《天部二》引“桓譚《新論》曰:通人揚子雲因眾儒之說,以天為蓋,常左旋,日月星辰隨而東西。”以上認為日月與恒星都在同一層天上,運行方向相同,而速度不同。這里用速度不同產生的相對運動來解釋日月落後於恒星轉動的情況,實際上把周年視運動與周日視運動混為一談。
帛書所載最後啟動的“天轉”是與“日行”逆向的,因此不屬於“左旋”說,而是迄今為止所知最早的“右旋”說。傳世文獻記載“右旋”說,約始於西漢緯書。《白虎通·日月》“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含文嘉》曰‘計日月右行也。’《刑德放》曰‘日月東行’”。《太平御覽》卷二《天部二》引楊泉《物理論》“故作蓋天,言天左轉,日月右行”。“右旋”說有一個經典而形象的比喻——“蟻行磨上”。《論衡·說日》載“日月…系於天,隨天四時轉行也。其喻若蟻行於磑上,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也。”“儒者說曰…天左行,日月右行,與天相迎…其取喻若蟻行於磑上焉”。《說文》“磑,磨也”。《晉書·天文志》說得更明白:
周髀家云…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回焉。
磨蟻的比喻形象生動地解釋了為什麼反向相轉卻同樣東升西落的現象。這個比喻最早是蓋天家發明的,用磨盤形象地比喻天蓋,渾天說以天球代替磨盤就輕而易舉地把蓋天右旋說變成了渾天右旋說[15],如云“今制日月皆附黃道,如蟻行磑上”(《宋史·律曆志》)。從帛書以天轉起晝夜消息來看,應該是蓋天派的“右旋”說。
(4)後共工時代與“晝夜消息”
克服共工推步難題的根本辦法是引入“晝夜”系統,上帝再次顯示神力,“乃逆日月以轉,相□息”。“□息”疑即“消息”。傳說“黃帝為蓋天”,《史記·曆書》載“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又曰“黃帝…名察度驗。”《漢書·律曆志》作“名察發斂”。“發斂”與“消息”互相同步。《周髀算經》載“冬至夏至者,日道發斂之所生也;至,晝夜長短之所極。”《續漢書·律曆志》“景長則日短,天度之端也,日發其端,周而為歲。”根據蓋天說理論,從夏至到冬至,太陽由內衡至外衡,其周日視運動圓周由小變大稱“發”,而其日道晝弧由大變小稱“消”;從冬至到夏至,太陽由外衡至內衡,其周日視運動圓周由大變小稱“斂”,而其日道晝弧由小變大稱“息”。故日道發而晝消,日道斂而晝息。後來“發斂”一詞渾天說仍然沿用,改指黃道去極度。如《漢書·律曆志》顏師古注“晉灼曰:蔡邕《天文志》‘渾天名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曆書集解》引“《續漢書》以為‘道之發斂,景之長短’,則發斂是日行道去極盈縮也。”帛文中的“消息”指晝夜長短變化,包括晝消夜息與夜消晝息,隱含著四季交替的信息。
按帛書所論,自上帝啟動天轉以生晝夜之後,推步曆法進入“後共工”時代,《淮南子·天文訓》稱“禹以為朝晝昏夜”,故“後共工”時代或可稱為大禹時代。此時最大的特點是引進晝夜系統,克服了共工“十日曆”的諸多問題。首先,晝與夜雖然分別有消長,但晝與夜相加等於1天,這個新的一“日”單位是等長的,可以用新單位把一年分為四季。四神推步靠步天得到“四時”,後共工時代靠步日得到“四時”,而共工推步既無星空參考,又無等時單位,故得不到準確的“四時”。
其次,後共工時代“有宵,有朝,有晝,有夕”,可據晨見昏伏星、昏旦或夜半中星直接推算出太陽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無需借用地平圈上的“十六分”方位。二十八宿位置有三種座標,一種是黃道座標,如《續漢書·律曆志》引“《石氏星經》曰黃道規牽牛初”,即戰國中期魏石申時代已有黃道座標。第二種是地平座標,如《周髀算經》記載二十八宿距度的測量方法,所舉例“牽牛八度”就是地平經差[16],我們認為所謂二十八宿“古度”[17],可能屬於蓋天說地平坐標系統。第三種是赤道座標,太初曆由落下閎測定的二十八宿“今度”,就是渾天說赤道坐標系統。不管使用哪種座標,太陽位置都已回歸星空的二十八宿之中,不再屬於“九州七舍”系統,因而更加直接和準確。
再次,就是提供了劃分四季的新方法——“晝夜消息”法等等。“天轉”啟動後,太陽的周日視運動在空中劃出一個平行於赤道的緯圈,位於地面以上者古稱“日道”今稱“晝弧”,位於地下者稱“夜道”和“夜弧”。如果太陽始終位於同一位置不移動,隨天轉而劃弧,其晝弧和夜弧的長短就一直不會有變化。然而太陽在黃道上每天移動一度,就必然引起“日道發斂”與“晝夜消息”的變化。
人們根據“晝消夜息”或者“夜消晝息”的信息,可以掌握四季的變化。這里需要計時工具配合,如水漏、沙漏或燃繩、測影等。把“晝夜消息”與四神時代的步天術結合起來,就是《堯典》的“四仲中星”法,這是經典的觀象授時方法。還可以根據北極璿璣四游加時、斗柄授時、日出入方位、日午時的晷影長短(太陽去極度的反映)等等來判斷季節變換。
總之,由於有日月和晝夜的產生,天轉和日行的參照,地球公轉與自轉的綜合效應得以充分顯現,各種觀象授時的傳統方法都能各顯神通,只有到此為止,作為宇宙起源的“時間”部分,才真正完備起來。
引入晝夜系統,給神話傳說帶來一個問題:太陽原本在同一“日舍”換班出入,現在的出入地點必須分開。太陽東升西落,出入地點相差約180o,按已有神話,陽烏每天負一日從東方天邊飛行到西方天邊,只需十天就把太陽全搬到西邊去了,東邊已無日可出。必須有一種大鳥,從天邊的地上把太陽搬回東邊去。這從考古學文化中似乎可以找到證明。山東大汶口文化大口尊上刻劃一種常見複合符號,上為日,下為山,中間或釋為鳥,表示陽烏負日在山上飛行[18]。仰紹文化廟底溝類型的汝州洪山廟遺址,出土彩繪陶缸上有大鳥馱日圖像[19],圖中間繪一隻大鳥,鳥頭前傾,兩腳前後張,似奮力在馱運一隻巨大的日輪;左右兩側各豎立一隻鳥,引頸張口,作迎送狀。據文獻載這種鳥應名“運日”。《淮南子?繆稱訓》“運日知晏(晴),陰諧知雨”。《廣雅》“鴆鳥,雄曰運日,雌曰陰諧。”《說文》“鴆,毒鳥也…一名運日”。《離騷》王逸注“鴆,運日也。”洪山廟彩陶上的“運日鳥”,描繪的正是從地上馱日行走的情形,應是從天邊把太陽搬回東方去,這樣就可以解釋神話傳說中,太陽何以層出不窮的問題。
4.餘論
楚帛書《時日》篇以神話故事的形式,表述了楚人關於時間起源的哲學思想和科學思考。剝開帛書的神話外衣,我們發現它具有豐富的科學內涵,它使用嚴格意義上的科學概念,運用嚴密抽象的邏輯推理,適當選用簡單的物理機制,合理解釋複雜的自然現象等等,這些非常類似於近代科學理論和科學假說的特徵。這使我們有必要重新認識神話與早期科學之間的關係,充分發掘神話傳說中隱藏的科學內涵和深刻思想,為歷史文化和科學思想研究開闢新的途徑。
楚帛書討論時間起源問題的方法,非常類似西方的“奧卡姆剃刀”原理(Occam's Razor)[20],這個原理由英國奧卡姆人、14世紀邏輯學家、聖方濟各會修士威廉(William of Occam,約1285~1347年)提出。他在《箴言書注》第2卷15題說“切勿浪費較多東西去做用較少的東西同樣可以做好的事情。”這個原理被簡述為“如無必要,勿增實體”(Entities should not be multiplied unnecessarily)。主張只承認確實存在的東西,剃除多餘無用的東西,被稱為“簡單有效原理”。“奧卡姆剃刀”促進經驗科學擺脫神學束縛,使科學、哲學從神學中分離出來,引發了歐洲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楚帛書假定在時間起源的第一階段只有“四時”,因而把“日月”、“晝夜”等複雜因素剃除掉,用一個僅僅能產生四季的“天動”機制來說明問題就足夠了。在第二階段增加實體“日月”,但“日行”本身可以產生“四時”,因而又剃除掉多餘的“天動”機制——通過奠定“三天”、“四極”使“天動”被制止下來。第三階段,僅用“日行”和“天轉”就足以解釋四季和晝夜的成因。楚帛書的思想方法,化繁為簡,簡明扼要,完全符合“簡單有效原理”。
楚帛書表達了一種宇宙進化論的觀點,認為宇宙是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複雜發展起來的。這種進化論是通過神創論的形式體現出來的,早期神的創造,遺留不可克服的問題,於是新的創造取而代之。例如四神時代的“天旁動”存在穩定性問題,於是“天動”被制止,由“日行”取而代之;而“日行”又造成共工時代的推步困難,因而啟動“天轉”以克復之,世界就這樣一步一步完備起來。這與基督教的神創論有明顯區別,基督教認為上帝用六天創造了全部世界,第七天休息,世界就形成了,沒有進化論的位置。中國的起源論也是一種神創論,不過眾神都參與了創造,最高神“帝”(或炎帝)有時命令下屬去創造,有時根據眾神的需要去創造,因此中國的“創世紀”是一個漫長的、英雄輩出、眾神創造的時代。
以往人們談到中國早期宇宙論總會提到“蓋天說”和“渾天說”兩種宇宙結構理論,並且一般認為蓋天說早於渾天說,渾天說晚至漢武帝時代才真正建立起來。然而關於渾蓋之爭的早期文獻記載非常缺乏,一般只能從西漢末年的緯書中找到隻言片語,楚帛書的發現,彌補了這方面的嚴重不足。今從楚帛書的時間起源論來看,它分別採用了渾蓋之說的有關部分作為立說依據。例如帛書說在“奠三天”“奠四極”之後,“帝夋乃為日月之行”,這時還沒有產生晝夜,而蓋天說是建立在“日道發斂”、“晝夜消息”的基礎之上的,沒有晝夜是不能用蓋天說理論來解釋的。不用“晝夜消息”而用“日行南北”解釋四季成因,正是渾天說的獨到之處,這表明渾天說完全可以早到先秦時代。楚帛書的發現,補正了文獻記載的缺失,對於我們重新認識上古時代的天文學思想提供了非常珍貴的資料。
(編者按:本文收稿日期爲2010年9月12日。)
[1]饒宗頤、曾憲通:《楚帛書》,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5年。
[2]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中華書局1985年。
[3]武家璧:《早期宇宙起源論的幾個特徵》,《自然辯證法通訊》2008年第6期,第72-75頁。
[4]李學勤:《補論戰國題銘的一些問題》,《文物》1960年第7期,第67-68頁。
[5]李學勤:《楚帛書中的古史與宇宙論》,張正明主編:《楚史論叢》第145-154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
[6]錢塘:《淮南天文訓補注》(二)第158頁,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1991年。
[7]武家璧:《含山玉版上的天文准線》,《東南文化》2006年2期,第18-25頁。
[8]劉次沅:《中國古代天象記錄中的尺寸丈單位含義初探》,《天文學報》1987年第4期;王玉民:《古代目視天象記錄中的尺度之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2003年1期。
[9]陳久金、盧央、劉堯漢:《彝族天文學史》第152-166頁,雲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10]中國天文學史整理研究小組:《中國天文學史》第74頁注②,科學出版社1981年。
[11]陳美東:《中國古代天文學思想》第475-483頁,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年。
[12]陳久金、盧央、劉堯漢:《彝族天文學史》第167頁,雲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13]金祖孟:《地球概論》第62頁,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
[14]鄭文光、席澤宗:《中國歷史上的宇宙理論》第99-104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
[15]陳美東:《中國古代天文學思想》第324頁,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年。
[16]錢寶琮:《蓋天說源流考》,《科學史集刊》(1),科學出版社1958年;又見《錢寶琮科學史論文選集》第388頁,科學出版社1989年。
[17]王健民、劉金沂:《西漢汝陰侯墓出土圓盤上二十八宿古距度的研究》,《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第59-68頁,文物出版社1989年。
[18]武家璧:《史前太陽鳥紋與迎日活動》,《文物研究》(第16辑)第35-50頁,黄山书社2009年。
[1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汝州洪山廟》,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袁廣闊:《仰紹文化的一幅“金烏負日”圖賞析》,《中原文物》2001年第6期。
[20]《簡明大不列顛大百科全書》(第12冊)第209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修訂版。
© Copyright 2005-2021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