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王堆《太一祝圖》考
作者:來國龍 發布時間:2014-11-10 14:52:42
(佛羅里達大學、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提要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重新綴合一塊關鍵性的題記文字殘片,嘗試對帛圖的定名及其可能的功能作出新的解釋,並試圖將中國古代方術的研究與藝術史的問題相結合,為“感神通靈”和中國早期繪畫傳統的起源與發展等問題的深入探討提供新材料。
關鍵詞:馬王堆、太一祝、圖文關係、早期繪畫
“It has long been an axiom of mine that the little things are infinitely the most important.” -Sherlock Holmes
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中出土大量帛書,備受學者矚目。然其中有一幅帛圖(彩圖1),長久以來尚未引起藝術史學者的足夠重視。這幅帛圖對中國早期藝術中文字與圖像的關係、人獸雜糅形象的意義,以及早期中國繪畫理論中的“感神通靈”觀念的討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1]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重新綴合一塊關鍵性的題記文字殘片,嘗試對帛圖的定名及其可能的功能作出新的解釋,並試圖將中國古代方術的研究與藝術史的問題相結合,來為“感神通靈”等問題的深入探討提供新材料。
馬王堆的帛書大都經折疊,存放於墓中東槨箱裏的一個長方形雙層漆匲内。層層叠壓的絹帛被揭開以後,都成碎片,需經綴合復原才能通讀。[2]本文討論的這幅帛圖為細絹彩繪,圖形以淡墨勾勒,然後填以朱紅、藤黃和花青等顔色。該圖的綴合整理工作是由湖南省博物館周世榮負責。周先生依據圖像、折痕、疊印痕跡等綫索,將其拼合為長43.5、寬45公分的帛圖。從整體來看,畫面共分為三層:上層殘損最嚴重,只留下中心人物的頭部及其兩側的雷公和雨師。該帛圖的中心人物是介於上層和中層之間的一個正面人像,頭戴鹿角,瞠目吐舌,雙手下垂,身著短褲,雙腳跨騎在一條黃首黑身的龍上。中層的一邊是兩個武弟子的正面像,頭戴奇特的山形冠,瞠目吐舌,一臂高舉,手持武器,另一臂下垂,身著上衣下裳(即裙)。中心人物的另一邊是同樣高舉一臂、題記文字稱為“虒裘”的人物,頭戴獨角帽,身著可禦弓矢的裘衣,側身面向中央。虒裘的左側是頭戴鹿角、表情怪異的神秘人物(其身邊可能原有題記,但已經殘泐不見),雙手把持兵器,身體向右,臉朝正面回轉,兩腮分別有一撮尖而長的鬍鬚。下層是黑龍龍身的下部,其左右兩側分別為一青龍和黃龍。[3]
該圖最早由周世榮1986年公開發表於《文物研究》上,圖版為黑白照片,質量很差,沒有引起學者注意。大概是因爲帛圖中心人物右腋下圓圈内標有“社”字,當時稱爲《社神圖》。[4]1990年周先生又發表專文介紹該圖的圖像和文字,並刊登了比較清晰的圖版和摹本。因爲圖上有天神“太一”、“雷公”、“雨師”等,又有“社”神,周先生認爲帛圖的中心人物既是天神太一,又是地祇社神,兩神合一,因稱此圖為《神祇圖》,並指出其中的文字大都“似祝由禁語,該圖具有辟邪的性質”。[5]
隨後,李學勤將該圖與湖北荊門所出的“兵避太歲”戈聯繫起來(圖1),認爲題記中的“太一”即“天一”,是太陰、太歲,稱此圖為《兵避太歲圖》。[6]李零則側重於武弟子等題記文字的避兵內容,認爲圖像的性質應該由文字的内容來決定。他說,“從全圖總題記和四武弟子像的題記來看,此圖顯然是以辟兵爲主要内容”,而且中心人物並非“天神、地祇合一”,而是因爲太一在天居中宮,而“社”即五行中位居中央的“土”,因此“太一”與“社”二者正好相應;太一代表北斗,中層武弟子等四神是與四方、四時相配的避兵之神,因此他推斷此圖應即《史記•封禪書》中提到的“太一鋒”,其性質是《辟兵圖》。[7]李家浩進一步推論帛圖中的“虒裘”可能即“蚩尤”的聲轉,[8]明確該圖内容是以太一爲主的避兵術,故稱為《太一避兵圖》。[9]三位李先生發表多篇論文討論該帛圖的文字與圖像,都對該圖的“避兵”性質沒有異議,而且都把該圖和所謂“兵避太歲”戈比較,把帛圖上的中心人物與戈援裝飾的頭戴羽冠、身著鱗甲、手握動物、腳踏日月的神人聯係起來討論,並結合相關傳世文獻的有關記載。[10]
最早對該圖的“避兵”性質提出異議的是陳松長和胡文輝。陳松長認爲古代“太一”是“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的至上神,單言避兵,“則似乎失之偏頗”,而且出行乃是該帛圖的重要主題,因此他建議依銘文定名的原則,取“太一”像題記文字中開頭“太一將行”四字,將該帛圖定名為《太一將行圖》。[11]胡文輝則根據該圖總體的性質認為此圖應該稱爲《太一出行圖》。胡氏的重要貢獻是把該帛圖和秦簡《日書》中記載的《出邦門》的巫術祝咒聯係起來,指出此圖描繪的是神(太一)的出行。[12]這一聯係對正確理解該圖的性質提供了一個廣泛的巫術文化的背景,並且同時指出該帛圖與“兵避太歲”戈沒有必然聯係。[13]隨後,饒宗頤也接受帛圖為出行圖的觀點,認爲帛圖的主題是用兵,而不是避兵。[14]
其他還有不少學者對該帛圖的性質、功能和意義進行探討。如李建毛認爲該圖是護身符籙;[15]連劭名以為《太一避兵圖》所繪的太一神就是南方楚墓中的鎭墓神;[16]楊琳認爲帛圖中心人物就是社神,該圖隨葬墓中是爲了威懾厲鬼,因而是《社神護魂圖》;[17]黃盛璋則把該圖定名為《兵禱太一圖》;[18]邢義田同意陳松長的結論,認爲該帛圖的功能是馬王堆3號墓墓主下葬時選用來保護墓主魂靈出行升天。[19]
上述研究加深了我們對該圖的認識。但是,正如邢義田指出,過去幾十年來,雖然不少學者對該圖作出了細緻的分析和命名的研究,然該帛圖的名稱至今仍衆説紛紜。該圖原件殘損嚴重,如何拼綴恢復其原貌和揭示圖文關係,仍有討論的餘地。該圖的性質和意義,學者之間也尚未達成共識。1992年,傅擧有、陳松長編著的《長沙馬王堆漢墓文物》一書,首次發表該圖的清晰彩照,當時筆者就讀於北京大學考古系,於李零先生寓所得觀此書。後又將該圖複印剪貼,揣摩有年。近年又數次造訪湖南省博物館,觀摩復核原件。本文即圍繞帛圖本身,僅就尚未徹底解決的幾個問題略陳管見。
一、帛圖的綴合與碎片位置的調整
和出土竹書木牘的研究一樣,研究帛書帛圖最基礎也是最關鍵的第一步,就是殘片的拼接綴合。雖然已有學者注意到周世榮的綴合和摹本都有問題,但是上述的討論都還是以周先生的復原圖為基礎。唯一對該帛圖的拼接提出新見解的,是李淞2009年發表的《依據疊印痕尋證馬王堆3號漢墓〈“太一將行”圖〉》一文。[20]李淞以最新出版的彩色圖像為資料,[21]用電腦軟件Photoshop處理,發現在殘損最嚴重的帛圖上層,有兩塊殘片(即所謂的“雷公”與“太一”的頭部)的位置需作重新調整。這兩塊殘片有左右對稱的疊印關係。因此,它們應該分別位於帛圖折疊的中軸綫的兩邊側。李淞已經指出,這樣的調整有多種方案可供選擇。為了達到降低帛圖的“完整性”和“完美性”的效果,他故意選擇了一種最爲極端的復原方案:即把“太一”的頭部移至畫面的左上角,與之對稱的“雷公”也相應地移至帛圖的右上角(圖2)。這樣帛圖中心人物(“太一”)就“身首分離”,同時也就避免了解釋帛圖時中心人物是太一還是社神的糾結。
但是,筆者認為李淞的這一復原圖還是存在不少問題。首先,他的極端方案因爲沒有確鑿的證據為支撐,雖有作者想要達到的很強的震撼力,但是並不能因此就“更接近原作”。他說“太一”的頭飾、面目表情、尺寸大小,“全無居高臨下的君主氣勢,喪失了等級差別,這不符合中國歷代的禮儀規制和圖像表現規律”,因此“太一”的面目“頗爲可疑”。[22]但是,事實上在圖像的性質還沒有完全弄清楚之前,就要以抽象的“中國歷代的禮儀規制和圖像表現規律”來判斷,這也是不足為據的。其次,他沒有考慮到帛圖右側邊緣、記載總題記文字的殘片也需要重新調整。如果按照筆者對總題記文字的調整,帛圖右側邊緣的總題記中,最下面一塊記載“太一祝曰:某今日且[行?] ”的殘片,應移至總題記開頭,即帛圖右上角的邊緣(圖3)。這樣一來,李淞想移至帛圖右上角的“雷公”殘片,就不可能安放在這一位置。再次,因為帛圖折疊的中軸綫恰好不是以中心人物為中心,而是在中心人物的中心綫稍偏右,因此李淞所發現的所謂“雷公”的面目與“太一”頭部的兩塊殘片,仍然有可能被安放在緊靠折疊中軸綫的兩側,而且“太一”的頭部仍然有可能就是中心人物的頭部。當然,這裡需要説明的是,這幅帛圖的完全綴合,尤其是殘缺最嚴重的上層的拼接,最理想的是利用更精密儀器的幫助、更細緻的分析(如絹帛的經緯、顏料的成分、疊印痕跡的分析等)。在這裡,我們只能就現有的材料與條件下所能做到的調整,談談我們的看法。
筆者對帛圖總題記文字的調整,主要是根據帛圖的內部綫索和外部證據。所謂內部綫索就是殘缺帛片之間的相互聯係。我們仔細觀察,可以發現記載“太一祝曰:某今日且[行?] ”的殘片和附近其他帛片沒有必然的隸屬關係。除了它應該是在帛圖右側邊緣、是縱向的總題記文字的一部分,我們也看不到其他任何放置該殘片的綫索。
所謂外部證據則是戰國秦漢時期祝禱文的文本結構。近年來戰國秦漢墓葬中出土不少于出行有關的祝禱文。[23]胡文輝的研究已經把該帛圖和戰國秦漢時期的出行時祝禱巫術聯繫起來。[24]其實帛圖的總題記也是一篇在舉行出行儀式時用的祝(咒)文,[25]這篇祝文的名稱就叫作《太一祝》。而且這是此類祝文的一個“範本”,是一個通用的祝文,並不是專門為馬王堆3號墓墓主而寫的,理由是文中使用了不定代詞“某”。許多類似的戰國秦漢祝禱文中,都有一些類似的現象。例如,戰國秦漢墓葬出土的宗教禮儀的“指南”與“手冊”、醫書醫方、法律文書範本等,經常用不定代詞“某”指稱不確定的人物、時間、地點等。[26]在實際的祝文中,這個“某”就會被出行者的具體名字所替代。這類祝文不但教人如何念祝辭(咒辭),而且還指導行術人怎樣表演巫術的儀式行爲,如畫地、披髮、禹步等,或者是使用呼喊吐納一類的巫術動作,如“臯”、“唾”等,最後念出的咒辭,而且還指示在執行完巫術活動後要“徑行毋顧”,不要回頭。因此,該帛圖上完整的出行祝文,應該是從“太一祝曰某今日且[行?] ”開始,而終於“徑行毋顧”。
出土的戰國秦漢祝文中,有一些是專門以“毋(或勿)顧”為終結的祝文。[27]如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載有多條治療“疣”疾的巫方,其中有兩方以“勿顧”結尾(依出土簡帛隷寫通例,□表示缺文,〼表示殘文,[ ]表示補出之字,釋文有疑問者加問號):
一,令尤(疣)者抱禾,令人嘑(呼)曰:“若胡為是?”應曰:“吾尤(疣)。”置去禾,勿顧。(一〇三)
一,以月晦日日下餔時,取凷(块)大如雞卵者,男子七,女子二七。先[以]凷(块)置室後,令南北[列](一〇五),以晦往之凷(块)所,禹步三,道南方始,取凷(块)言曰凷言曰[三字衍文]:“今日月晦,靡(磨)尤(疣)北。” 凷(块)一靡(磨)(一〇六)。已靡(磨),置凷(块)其處,去勿顾。靡(磨)大者(一〇七)。[28]
馬王堆漢墓出土的《胎產書》中求子的埋胞巫術,也用“勿顧”結尾:
女子鮮子者產,令它人抱其□,以去□□濯其包(胞),以新布裹之,為三約以斂之,入□(三三)中,令其母自操,入谿穀□□□之三,置去,歸勿顧;即令它人善貍(埋)之(三四)。[29]
敦煌懸泉漢簡第266號簡記載巫術療疾的禁咒方,同樣要求行術者在做完法術後,“疾去勿顧”:
入廁,禹步三。祝曰:入則謂廁哉,陽謂天大哉,辰,病與惡入,疾去毋顧。[30]
又如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一〇二叁至一〇七叁簡:
[出]邦門,可〼(一〇二叁)行〼(一〇三叁)禹符,左行,置,右環(還),曰□□(一〇四叁)□□右環(還),曰:行邦〼(一〇五叁)令行。投符地,禹步三,曰:皋(一〇六叁),〼[投]符,上車,毋顧(一〇七貳)。[31]
對於最後一條《出邦門》,劉樂賢和胡文輝都已經正確指出,是出行時施行的是一種巫術儀式和動作,通過人爲的巫術和咒語,以期達到出行無災無害、最後能順利歸來的目的。[32]他們還將秦簡中的《出邦門》與相關敦煌文書、後世數術、醫療文獻進行對比,發現很多都有“咒畢便行,慎勿反顧”一類的禁忌。學者已經指出,“毋顧”是一個有特別巫術意義的行為,是在出行、療疾等事項所舉行的巫術儀式中行術者必須遵守的禁忌,而且往往是在完成某項主要的巫術活動後離開的時候,要“毋顧”。對於“徑行毋顧”在該帛圖中的特定巫術意義,我們下文還會再討論。在這裡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馬王堆帛圖上的《太一祝》總題記應該調整為(圖4):
《大一祝》曰:某今日且[行?],神(?)〼將(?)承弓,[33]禹先行。赤包白包,[34]莫敢我鄉(嚮)。百兵莫敢我[傷]。[35]〼狂謂不誠,北斗為正。即左右唾,[36]徑行毋顧。
更有意思的是,帛圖不僅僅是對《太一祝》文的圖像解釋,還包括了其他圖像和題記。帛圖的上層在太一、雨師、雷公的頭像附近分別有題記:
太一將行,何(荷?)日,神從之〼 (圖5)[37]
雨師:光風雨電,〼從者死,當[者有咎],左弇其右□□(圖6)
雷[公] 〼 (圖7)
中層在兩武弟子像和虒裘像的邊上分別有(圖8a-c):
武弟子:[38]百刃毋敢起,獨行莫〼
我(?)□,百兵毋童(動)〼禁
我虒裘,[39]弓矢毋敢來
下層黃龍和青龍邊上分別有(圖9a-b):
黃龍持鑪
青龍奉容(鎔)[40]
因此,《太一祝》文本的性質,和考古發現的其他類似的祝禱文一樣,是記錄指導出行時施行的一種巫術儀式中所作動作與所念咒語的一個通用文本。該帛圖描繪的主要是出行前的儀式,是對《太一祝》的出行儀式的一種視覺表現,其目的是幫助出行者想像旅途中跟隨他的諸多神祇隨從,保護出行者一路消災免禍。雖然中層和下層的圖像和文字有明顯的避兵内容,但是,避兵只是該巫術儀式的一個組成部分,帛圖的整個意圖不只是為了避兵,而是爲了護佑出行者。
二、帛圖中心人物究竟是誰?
迄今對馬王堆帛圖的討論中,爭議最大的是中心人物的身份問題。對此上述學者有不同的意見。例如,周世榮認爲帛圖中心戴鹿角的神人兩側“太一”與“社”並見,因此它是兩神的結合,是“楚人所崇拜的火神和太陽神”;[41]李學勤曾誤認中心人像邊上的題記中“太一”爲“天一”,以爲它和荊門銅戈援部的神異人物相同,都是“太歲”的形象。[42]其後,李零、陳松長、李學勤、李家浩、饒宗頤、邢義田等都認爲中心人物即“太一”,而李建毛、胡文輝、楊琳等認爲它是“社”神。也有學者試圖調和兩說。胡文輝則從傳世古籍中找出“禹即社神”的説法,認爲帛圖的中心人物就是“社”神,也就是禹。[43]林巳奈夫也認為中心人物是“太一”,是天神中的最尊貴的“帝”的形象。[44]
筆者認為,這個中心人物可以是上述所有這些身份的神,但是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出行者,是一個凡人。這個中心人物的形象描繪的是被天神、地祇或禹“附體”的出行者。要正確理解這一説法,我們必須先來談一下上古中國宗教中神人關係中的“降神附體”(spirit-possession),也就是“憑依”的觀念。
作爲一個古老而基本的宗教實踐,“降神附體”的觀念上可以追溯到史前時期,下則延續到近現代。[45]中國上古商周時代的祭祀祖先的儀式中,祖先的神靈通常會附著在由活人扮演的“尸”身上。“尸”一般是家族中的年輕成員,按照規定的儀禮程式,用自己的肉身來扮演祖先。當然,“憑依”是要有條件的,即扮演的人必須是“孫”,無孫則取于同姓。所以這裡強調的是“血緣”關係。[46]春秋時期,傳統的血緣觀念開始動搖,鬼神的憑依開始強調行爲人的道德修養。[47]根據《左傳》、《國語》等早期文獻記載的鬼故事,死於非命的普通男女也會變成惡鬼,並“憑依”在活人身上,成爲厲鬼。[48]甚至像石頭這樣沒有生命的物體,也能被鬼魂附體而開口說話。[49]到了戰國時期,用“尸”的做法以及集體祭祖風俗衰落了,但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發展,即“降神附體”的觀念延伸到了宗教儀式的其他領域。通過新的巫術儀式手段,也可以讓鬼神附在活人的身上。換句話說,人可以通過各種方術手段或儀式活動,擁有鬼神的力量。這便是“自我神化”(self-divinization)思想的宗教及儀禮背景。[50]在戰國秦漢文學作品中,有不少描寫神靈或者詩人自況神仙遠遊出行儀仗,其中經常有雷公、雨師等眾神護衛。如《楚辭·遠游》:
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 問太微之所居。……駕八龍之琬琬兮,載雲旗之逶蛇。……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風伯為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時噯曃其矘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眾神以並轂。……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以為衛。……[51]
《遠遊》一詩先敍述主人公遠遊的動機,然後介紹遠遊前的準備,最後描寫遠遊的過程。主人公在眾神護衛下的出行儀仗,正是馬王堆《太一祝》帛圖所描繪的場景。這裡的主人公是詩人、也是出行者。在《韓非子·十過》的類似描寫中,出行者是黃帝:
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 畢方並轄, 蚩尤居前,風伯進掃, 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52]
這個出行者還可以是「大丈夫」。如《淮南子·原道》:
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 澹然無慮;以天為蓋, 以地為輿;四時為馬, 陰陽為御;……令雨師灑道, 使風伯掃塵, 電以為鞭策, 雷以為車輪。上游於霄雿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53]
而東漢蔡邕的《祖餞祝文》,也是出行前的一篇祝文,其內容與《太一祝》最為接近:
令歲淑月,日吉時良。爽應孔嘉,君當遷行。神龜吉兆,休氣煌煌。蓍卦利貞,田見三光。鸞鳴雍雍,四牡彭彭。君既升輿,道路開張。風伯雨師,灑道中央。陽遂求福,蚩尤辟兵。倉龍夾轂,白虎扶行,朱雀道引,玄武作侶。勾陳居中,厭伏四方。往臨邦國,長樂無疆。[54]
與上面描寫的出行者類似,馬王堆《太一祝》帛圖上描寫的出行者,是透過操弓射矢、念咒語、左右唾等巫術動作,而被太一、社神或禹等神靈所附體,在旅途中得到他們的庇佑。[55]而太一和社神分別是戰國以來的神譜中天神與地祇中的兩個領頭人物,所以代表的是天地的神靈,也就是“神從之”中的“眾神”。根據當時“降神附體”的觀念,其實帛圖的中心人物既可以是“太一”,也可以是“社”神,代表天神地祇,但是它最主要代表的,是出行者,是一個人間的凡人。這幅帛圖是對旅行者出行儀仗的具體描繪。這裡我們有必要進一步來解釋馬王堆《太一祝》中“徑行毋顧”的巫術意義。
三、“徑行毋顧”的巫術意義
前面已經提到“毋顧”作爲一種有特別巫術意義的行為,是在出行、療疾等事項所舉行的巫術儀式中行術者必須遵守的禁忌。這種禁忌在中西古代文化中都有不同的體現。希臘、羅馬和西方古代文化中,最有名的兩個故事:一是古希臘神話中恩愛夫妻奧菲斯(Orpheus)和優麗狄絲(Eurydice)的故事。奧菲斯去冥府解救死去的愛妻,冥王要求兩人在抵達地面之前,奧菲斯不可以回頭看跟隨其後的尤麗狄絲,也不能和她說話,否則尤麗狄絲將再也不能復活。一是《聖經》(創世紀19.26)故事中羅得(Lot)和妻子逃離索多瑪(Sodom)城時,“羅得的妻子在後邊回頭一看,就變成了一根鹽柱」。對於這兩個故事中“毋顧”的意義學者有不同的解釋。Jan N. Bremmer對“毋顧”(don’t look back)這一母題在希臘、羅馬文獻中流傳進行了研究,認為很可能起源於古希臘,並總結了這一母題出現的幾種情形:一是與冥界有關;二是與巫術魔法有關;三是與淨化有關的;四是與外出旅行有關;五是與創世有關。[56]其中一些與分離有關,如淨化、外出旅行和魔術;有一些是爲了逃避或回避,如冥界和創世。但是這一禁忌還可能有更現實的原因,即人在逃離時,最快的方式可能就是急行勿顧。[57]
除了前面提到出土文獻中出行、療疾中的“毋顧”的禁忌,傳世早期文獻中也有和《聖經》中羅得妻子類似的故事。如《淮南子·俶真訓》記載 :“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漢代的學者高誘注曰:
歷陽,淮南國之縣名,今屬江郡。昔有老嫗,常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謂嫗視東城門閫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嫗便往視門閫。閽者問之,嫗對曰如是。其暮,門吏故殺雞血涂門閫。明旦,老嫗早往視門,見血,便上北山,國沒為湖。[58]
劉文典指出,唐代馬總編撰的《意林》注引與此略同,惟末有“母遂化作石也”六字。這樣,唐代流傳的本子似乎更接近《聖經》故事。另一則類似的故事則見於《呂氏春秋·本味》,記載伊尹之母身化爲空桑的故事:
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59]
這兩個故事的來源與流傳,我們現在還不清楚。我們也沒有證據可以證明中國古代叙事中的“毋顧”母題和希臘、羅馬神話或《聖經》故事有任何歷史聯係。但如上述希臘、羅馬及《聖經》的例子,中國的例子也大致可以從禮儀、心理、巫術等方面來解釋,而且這幾個方面很可能都是互相關聯的。
比如《論語·鄉黨》有“車中不内顧”一句,歷代學者有不同的理解。[60]南朝梁學者皇侃說:“内猶後也,顧,回頭也。升在車上,不回頭後顧也。所以然者,後人從己者不能常正。若轉顧見之,則掩人私不備,非大德之所為,故不為也”。[61]這裡好像是出於禮貌,不在車内回頭顧視。楊樹達又引一段《左傳》的故事來討論這個問題。[62]《左傳·宣公十二年》:
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63]
逢大夫和兩個兒子在逃命的時候,叫兒子不要回頭看,但是這兩個不聽話的兒子偏偏回頭顧視,而且說趙旃就在後面。這樣迫使逢大夫停下車來,叫兩個兒子下車,而讓趙旃上車得以逃脫,逢大夫的兩個兒子卻死於非命。這裡我們不清楚逢大夫是出於道義,不能見死不救,所以要他二個兒子不要回頭看,還是有其他巫術的原因。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行篇》也有解釋出行者出門後“毋敢顧”的原因:
凡民將行,出其門,毋敢顧,毋止。直述(術)吉,從道右吉,從左吝。少(小)顧是胃(謂)少(小)楮,吝;大顧是胃(謂)大楮,凶。[64]
秦簡整理小組正確指出“楮”即“佇”,是“停留”的意思。因此,小顧就是小停,有小不利;大顧就是大停,有大凶。雖然還是沒有解釋爲什麽,但是“顧”會給出行人帶來災殃。[65]中世紀的道教經典也指示燒香及退出淨室時,“勿反顧,反顧則忤真炁,使致邪應也”。[66]
劉樂賢則根據唐代孫思邈《備要千金方》卷二十七《黃帝雜忌法第七》:“行及乘馬,不用回顧,則神去人不用,鬼行踖栗”以及《雲笈七簽》卷三十五“禁忌篇”:“或運行、乘車馬,不用回顧,顧則神去人”,推測古人有“顧”則神靈離體的觀念。[67]這些雖然都是較晚的經典,但有可能保留了較古老的巫術意義。“顧則神去人”這樣的解釋更切合馬王堆《太一祝》中“徑行毋顧”的巫術意義。出行者透過巫術表演,讓神靈附身,應該徑行毋顧,否則已經附著在身的神靈就可能離開,巫術表演的魔力也就失效了。
四、帛圖中心人物形象與包山遣冊記載行器的聯繫
我們還可以從馬王堆《太一祝》帛圖上中心人物的形象,與包山楚墓遣冊所列“行器”的聯繫,來支持帛圖上的中心人物就是個出行者這一結論。這批遣冊發現於湖北荊門的包山2號戰國楚墓,記載的是隨葬器物的清單。包山2號楚墓和馬王堆3號墓相距約一個半世紀,都是在戰國秦漢時期的南方廣義的楚文化範圍内,因此在某些宗教文化上可能保持了一定的連續性。包山2號墓遣冊中的第一支簡(259號簡)記錄如下:
相徙之器所以行:一桂(觟、獬)冠、組纓。[68]一生繱之厭。二狐睪(襗)。[69]二紫韋之帽。一會
由於地下保存的狀況不好,許多有機物的隨葬品都已腐爛消失,而且楚簡文字難識,我們還不能明瞭遣冊所記的全部物品,但是大致的内容仍可了解。令人驚訝的是,從這一類簡所稱的“相徙之器所以行”的“行器”中,我們看到的不是一般想像中的車馬和其他旅行用具,而是些帽子(獬冠)、褲子(狐襗)、鞋子(屨)、毛巾、梳子(櫛、笲)、枕頭、折疊床、燈等之類的日常生活用品。戰國時期的貴族墓中充滿了個人日常用品,尤其是衣物和飾品。其中的觟冠和狐襗最值得注意。戰國時期的望山2號楚墓的遣冊也記載了兩件作為陪葬品的獬冠(62號簡)。[71]“獬冠”一詞也出現在傳世文獻中。如《淮南子·主術》中提到“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獬是傳説中的一種獨角神獸,戰國時期的青銅器裝飾中以及後來漢代壁畫及單獨雕塑中都有類似的形象(圖10)。[72]學者根據漢代經學家的注釋,推斷出獬冠事實上是一種頂上有角的帽子。[73]遺憾的是,由於墓葬中保存條件的限制,發掘者並沒能在包山或望山墓的隨葬品中找到這樣的帽子。但在包山2號墓的北槨箱中,卻發現了一個雕刻有三龍相纏的角形器(圖11),以及一些個人飾品,包括一頂假髮、四件玉飾和骨飾等,皆出於北室中一個紅黑相間彩繪的漆竹笥內(M2:431)。這個角形器原本很可能就是裝在獬冠上的角,即遣冊上所列的獬冠之上的獨角。[74]這頂戴獨角的帽子,可能就是包山2號墓墓主邵
儘管馬王堆《太一祝》帛圖的中心人物頭上戴的Z字形鹿角與邵
五、人獸雜糅圖像的魅力
馬王堆《太一祝》帛圖上的七個神靈,除了形象不清楚的雷公和雨師以外,都是人獸雜糅的形象(hybrid images)。在我們所討論的早期中國這個時段中,即從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前2世紀,在視覺文化上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幻想的、兼具人獸特徵的雜糅圖像的流行和鬼神的人形化。如湖北隨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內棺表面所繪的漆畫神異圖像(彩圖2),[76]以及子彈庫楚帛書四周所繪與十二月份有關的神像。前面提到的湖北荊門出土的戰國時期的所謂“兵避太歲”戈,在戈援兩面都裝飾正面的半人半獸像,頭戴羽冠,身披鱗甲。[77]戰國時期楚地流行的所謂“鎮墓獸”(筆者認爲它們事實上是“求子之神”,詳另文)也表現成一種融合了不同動物特徵,包括麋鹿角、蛇頭、人臉等的半人半獸形態,後來又加入的更多的人形的元素,如怪臉、吐舌、卷鼻、齜牙等。早期中國藝術中為什麽以這種人獸雜糅的方式來呈現神靈?
此前對人獸雜糅圖像的研究中,有學者用薩滿教理論來解釋人形與獸形的這種奇特結合。張光直等學者認為這些半人半獸圖像描繪的是處於從動物向人過渡的過程之中的薩滿教巫師。[78]魯惟一(Michael Loewe)則認為半人半獸的形象源於人類對動物的認同(比如圖騰崇拜)以及對早期中國神話的歷史化,因而動物形象是被擬人化了。[79]杜德蘭(Alain Thote)則將半人半獸圖像的突然出現歸功於為被楚文化吸收的當地少數民族的文化影響,以及可能來自近東或中東藝術的影響。[80]
但近幾十年來,薩滿教與圖騰信仰理論在早期中國研究中的運用備受質疑。對早期中國神話和神祇的歷史化,也不足以解釋這個人神混雜的現象。因為我們無法證明在此之前曾經存在一個完全是動物或神話為主的文化系統,到後來才被改造成了另一個以人或歷史敍事為主的文化系統。此外,儘管杜德蘭所討論的東周刻紋銅器有可能是本地生產的,但是我們也沒法證明半人半獸圖像和相關的文學描述(如《山海經》)就一定是屬於某個特定地方的文化特點。事實上,這些人神雜糅圖像的出現是一個廣泛普遍的現象,不僅僅局限於視覺藝術,也發生在早期的文學作品,如《左傳》、《山海經》等。正如蒲慕洲所說的:“《山海經》中半人半獸的神靈形象不是某位作者的創造,而是發源於戰國時期共同的信仰背景”。[81]
筆者認為這一“信仰背景”至少包括以下三個方面。首先,人像作為藝術表現的对象,其社會價值越來越得到提高,人們對人像的態度不斷發生變化。人像社會價值的提高是因為死者家屬試圖確認、控制與協助正在升天、從生到死的過渡階段的死者。儘管戰國時期對人像的態度仍帶有以濃厚的巫術控制的意味,但這種態度已經開始動搖,而更多的是對人像的親近、憐憫與同情。因此,從這個時期開始,人像的力量對早期中國藝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其次,已如前所述,戰國時期“降神附體”宗教觀念有了一個嶄新的發展,而且這一發展對人們的生活和行為產生相當的影響。
最後,也是戰國時期“信仰背景”的第三個要素,即人獸雜糅圖像對當時人們的巨大的心理影響力。20世紀50年代,Alfred Salmony對“鎮墓獸”(即他所謂的“鹿角與舌頭”母題)進行了一項先驅性的研究。[82]他採用傳播論的方法,引用當時流行的“藝術母題傳播論”,得出了中國的鹿角與吐舌母題是受印度文化的啟發、從中亞傳入的結論。幾個評論Salmony書的學者不同意他的觀點,他們同時指出,應該先找到人類的“共同根基”或“共同遺產”,再來解釋藝術母題之間的相似性。[83]而半人半獸形象對人的心理影響,其實便屬這種“共同根基”或“共同遺產”。
長期以來精神分析學家、文化史學者、藝術史學者一直關注的一種名為“美杜莎效應”(the Medusa Effect)的文化現象(彩圖3)。[84]弗洛伊德在一篇未完成的遺作的簡要提綱中,最先指出美杜莎的長滿令人噁心蛇髮的形象具有驅邪的效應。[85]這些被學者稱為“驅邪形像”,“往往是人臉、生殖器和危險動物圖像,讓觀看者產生反感、無力、驚懼或敬畏的感覺”。[86]也有學者對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學與文化現象的分析,認爲“美杜莎效應”反應了當時人們對於西方文化及社會現實(如工業革命與現代城市的發展、女權主義的興起、殖民主義的擴張、性壓抑與性權力衝突等等)的深層的矛盾心理(ambivalence)。[87]在對裝飾藝術的心理學研究中,貢布里希(E. H. Gombrich)還進一步指出,中世紀寫本頁面邊緣的半人半獸圖案和文藝復興裝飾中的奇異風格“保留了活躍的‘驅邪’傳統”。[88]近來藝術與科學(特別是神經科學)研究的進展極大地提高了我們對這種“共同遺產”的認識。
Joseph E. LeDoux和其他生物科學家研究了人腦恐懼反應的神經心理機制。他們發現,控制恐懼反應的核心要素是大腦中的杏仁體。有兩條傳送視覺信息的通道——皮質和皮質下通道。皮質通道是指視覺上的刺激首先進入丘腦,丘腦再將粗略的、原始的信息直接傳達到杏仁體。視覺信息傳達的第二條通道──皮質下通道,則速度較慢。視覺上的刺激首先進入丘腦,傳達到視覺皮層,然後再傳達到杏仁體。這條通路可以對所見事物進行真實再現,幫助我們準確分辨,看到的東西到底是一條蛇,還是一根木棒或草繩。LeDoux將第一條通路稱為“迅速的下意識反應機制”,它使大腦開始對可能的危險作出下意識的迅速反應。視覺信息被傳送到杏仁體,可以使心律加快、血壓上升,並使肌肉收縮,形成經典的“或戰或逃的恐懼反應”。這種“迅速的下意識反應”不僅出現在人看到蛇或類似於蛇的東西(如木棒或草繩),也會出現在當人看到令人懼怕的臉面、或者是威脅到自己生命安全的兇猛動物以及其他危險物的圖像等。因此,早期中國的神靈之所以以半人半獸的形式來呈現,很可能是因為這些危險的動物所具有的特徵,能夠下意識地引起恐懼感和敬畏感。[89]
雖然這樣的恐懼反應的神經心理機制是人類所共有的,但是在人類發展的不同時期、不同文化環境中,卻表現出不同的形象特徵。戰國秦漢時期這一現象在南方楚地特別流行,可能是和當時人們對死者及神靈世界的又敬又畏、又憐又愛的矛盾心理有關。[90]一方面是對於死者及神靈世界的恐懼與厭惡,但是另一方面又要利用它們來驅除邪惡,保護自己。
馬王堆《太一祝圖》上的人獸雜糅圖像,在戰國到秦漢的視覺文化演化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過渡角色。這裡的所表現的,不完全是受膜拜的神靈本身的圖像,也不是“圖像方術”的對象,而是代表一個被神靈附體的出行者,是生者可以認同的一個凡人。這種從圖像的魔力向一種新型表現方式,即人形與動物特徵雜糅的半人半獸圖像的轉變,標誌著中國早期的藝術表現觀念在戰國與漢初發生了重要變化。
六、結論
綜上所述,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的、學者稱之爲《神祇圖》、《辟兵圖》、《太一出行圖》等名稱的那幅帛圖,按照其内容和右側邊緣的總題記,應該重新命名為《太一祝圖》,它的性質和其他戰國秦漢時期出土的出行祝文一樣,是用以指導某種巫術儀式的通行範本,其具體內容則是記錄出行者在該儀式中應做的動作及所念的咒語。根據同時期出行祝文的結構,筆者認爲該帛圖上右側邊緣的總題記應該始於“《太一祝》曰:某今日且[行?] ”,而終於“徑行毋顧”,因此帛圖上的相應碎片的位置也應該作相應調整,即現位於右側邊緣最下方記載“《太一祝》曰:某今日且[行?] ”文字的殘片應該挪到右側邊緣的最上方。帛圖的中心人物既可能是太一、也可能社神,但最終所表現的都是出行者,是出行者被太一、社神等神靈“憑依”以後的形象。祝文最後的“徑行毋顧”,正是告誡出行者,在通過巫術表演降神附體之後,應該徑行毋顧,不要回頭,以免已經附體的神靈脫身而去。通過與包山2號楚墓出土的遣冊上有關“行器”記載的比較,我們發現馬王堆《太一祝圖》上所繪的中心人物,其實就是一個全副武裝,頭戴獬冠、身著短褲、跨騎神龍的出行者的形象。最後筆者利用《太一祝圖》來説明戰國、秦及漢初流行的以人獸雜糅圖像來表現神靈的形象,可能是和戰國秦漢時期人們對於死者和神靈世界的矛盾心理有關。此圖是一張供個人使用的小圖,也可能是在舉行出行禮儀之前,用來作心理準備,出行者將自己想象成太一、社神的化身,駕龍出行,雷公、雨師護駕,四個武弟子護衛,青龍黃龍銷熔兵器。
最後應該指出的是,類似這種通過巫術表演、口念咒語等修行方法以期得到“刀槍不入”等護身的特異功能,後世稱“符法”(talismanic methods),在中國道教與民間宗教中一直流傳。近如義和團的“刀槍不入”的“避兵”術以及日治時代臺灣的噍吧哖事件中,此類“符法”都曾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91]
English Summary:
The Mawangdui Diagram of the Taiyi Incantation
Among the silk manuscripts excavated from Tomb at Mawangdui is a small diagram that has been overlooked by art historians. In previous discussions on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pictorial tradition, scholars have focused on the technical aspects of the illusionist presentation, the depiction of depth on two-dimensional surfaces, and so forth. Very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use of imag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both text and contex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Tomb diagram in both the ritual context of spirit travel and the evolution of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 linking the image to the text of a contemporary incantation. The diagram occupies an important transitional role in the evolution of visual culture in early China. Here the main figure is no longer the subject of “image magic” but is instead a traveler, someone with whom the living could identify. Here we can see a shift away from the magical potency of images to a new kind of figural representation, in which hybrid images fused anthropomorphic form and zoomorphic attributes.
Keywords: Mawangdui, Taiyi incantation, text and image, early pictorial art
附記:本文首刊於《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輯刊創刊號,第1輯(2014),頁1-27。
本文的主要內容曾在幾次會議、演講、座談討論等不同場合口頭發表。在寫作和修改過程中有得到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張瀚墨、蔡亮、謝明良、繆哲等先生的幫助,謹致謝忱。
彩圖1 馬王堆《太一祝圖》,西漢(約公元前168 年),1973 年湖南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館藏。

彩圖2 曾侯乙墓棺飾,戰國(約公元前433 年),1978 年湖北隨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館藏。

彩圖3 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 約1618 年,《美杜莎頭》(Head of Medusa),68.5×118 cm,奧地利維也納The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藏。

圖1 “兵避太歲”戈,戰國,1960 年湖北荆門漳河車橋戰國墓出土,湖北荊州地區博物館藏。

圖2 李淞《“大一將行”圖》復原圖,引自《美術研究》2009 年第2 期。

圖3 馬王堆《太一祝圖》局部,“太一祝曰”題記殘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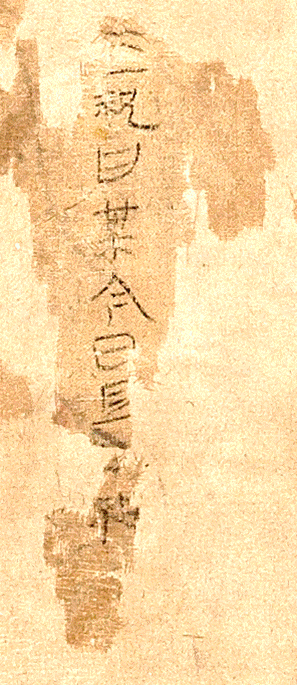
圖4 馬王堆《太一祝圖》局部,重新復原的“太一祝”總題記。



圖5 馬王堆《太一祝圖》局部,“太一”頭像及題記殘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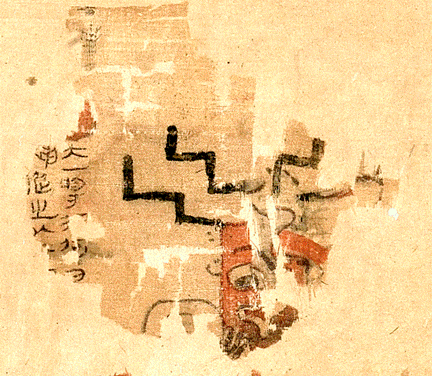
圖6 馬王堆《太一祝圖》局部,“雨師”題記殘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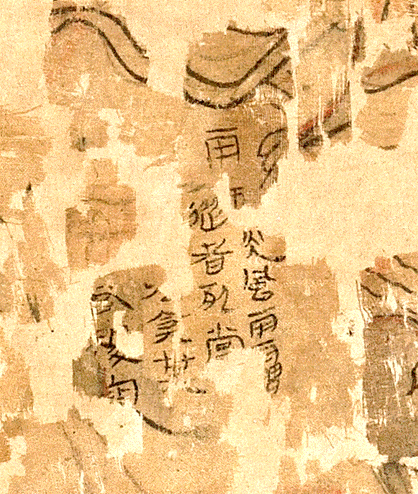
圖7 馬王堆《太一祝圖》局部,“雷[公]”題記殘片。

圖8a-c 馬王堆《太一祝圖》局部,“武弟子”、“虒裘”題記殘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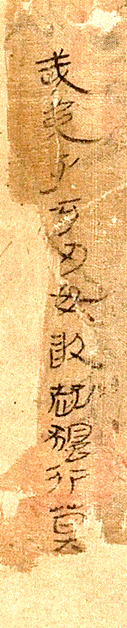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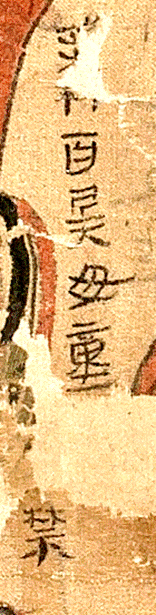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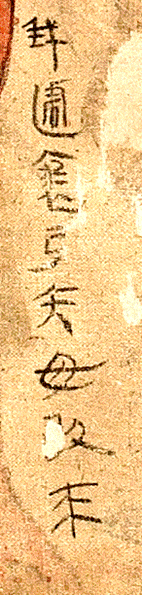
圖9a-b 馬王堆《太一祝圖》局部,“黄龍”、“青龍”題記殘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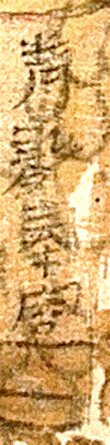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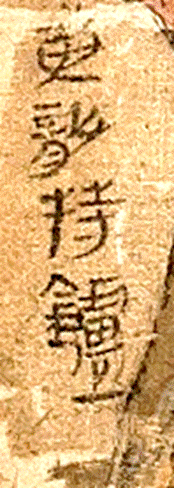
圖10 青銅獨角獸,東漢,1956 年甘肅酒泉下河清出土,高24.5 釐米、長74.7釐米,甘肅省博物館藏。

圖11 三龍相纏的角形器,戰國(約公元前316 年),1987 年湖北荆門包山2號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館藏。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4年11月9日17:04。)
[1]對中國早期繪畫中“感神通靈”觀念的討論,見錢鍾書,《管錐編》,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711-718;Munakata Kiyohiko (宗像清彥), “Concept of Lei and Kan-lei in Early Chinese Art Theory.” In Susan Bush and Christian Murck, eds., Theories of Arts i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05-131; 石守謙,《“幹惟畫肉不畫骨”別解──兼論“感神通靈”觀在中國畫史上的沒落》,《藝術學研究年報》4 (1990),頁165-191;鄭岩,《逝者的“面具”——再論北周康業墓石棺床畫像》,收入巫鴻、鄭岩主編,《古代墓葬美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第一輯,頁217-244,特別是頁236-237。錢鍾書廣征博引中西古今史料,但並未對此現象作進一步的闡釋;宗像清彥側重於從漢代“天人感應”哲學思想來理解;石守謙的研究集中於中國中古時期繪畫史料的梳理與解釋;鄭岩已經指出這一觀念不限於中古時期,其根源應在上古。
[2]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頁42-43,87-91。
[3]由於帛圖埋葬於墓裏長期浸泡在棺液中,某些顔料易發生化學反應,因此下層中間的龍原來是否就是黑色尚不能確定。關於青色顔料在馬王堆漢墓棺液中變黑的討論,參看程少軒,《馬王堆漢墓〈喪服圖〉新探——復原一份反映西漢初期家族權力結構的禮儀圖像》,延世大學人文學院研究院“權力的投影:中國的制度、政策與文字”學術交流會會議論文,2014年3月28日。
[4]周世榮,《馬王堆漢墓中的人物圖像及其民族特點初探》,《文物研究》1986年第2期,頁71-78。
[5]周世榮,《馬王堆漢墓的“神祇圖”帛畫》,《考古》1990年第10期,頁925-928。
[6]李學勤,《“兵避太歲戈”新證》,《江漢考古》1991年第2期,頁35-39。
[7]李零,《馬王堆漢墓“神祇圖”應屬辟兵圖》,《考古》1991年第10期,頁940-942。收入李零《入山與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203-207。釋文參見李零,《中國方術考》(修訂本)(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頁77-79。
[8]李家浩“虒裘”可能即“蚩尤”的推論是完全可能的,但他的論證和理由,如“古代文字因聲母相同或相近而通用的情況屢見不鮮”,則是不完全確切。雖然古代從“之”聲之字與從“虒”聲之字的聲母確實很多相同,但是兩個字不能因爲聲母相同或相近就可以通用(或稱所謂的“雙聲通假”)。事實上很多這樣通假的例子,是因爲連讀音變而造成的。“虒”字的讀音受了後面緊跟著的“裘”(之部)的影響,而音變成之部的“蚩”。“裘”(B-S*gʷə)、“尤”(B-S*ɢʷə)古音至近。參見李家浩, 《論〈太一避兵圖〉》,《國學研究》第一卷(1993),頁285-286。本文所用上古音的擬音是根據白一平和沙加爾的系統(Baxter-Sagart Old Chinese reconstruction, version of 20 February 2011,簡稱B-S)。對古文字中的連讀音變現象的討論,見來國龍,《說“殺”“散”,兼談古文字釋讀中的通假字問題》,《簡帛》第4輯 (2009),頁315-331。“蚩尤”這一名稱出現在春秋戰國之際的“魚鼎匕”和漢初馬王堆帛書《經》(舊稱《十六經》或《十大經》)中。傳世典籍中“蚩尤”有古之天子、九黎之君、炎帝之末諸侯、神農時諸侯、始造兵者、庶人之貪者、熒惑之精等多種身份,因此後世文獻中的“蚩尤”很可能有不同的來源。參看李零,《考古發現與神話傳説》,收入李零,《待兔軒文存•讀史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43—70, 特別是頁62-65;宗福邦、陳世鐃、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2006-2007。
[9]李家浩,《論〈太一避兵圖〉》,頁277-292;李家浩,《再論“兵避太歲”戈》,《考古與文物》1996年第4期,頁28-32。
[10]李零,《湖北荊門“兵避太歲”戈》,《文物天地》1992年3期,頁22-24;李學勤,《古越閣所藏青銅兵器選粹》,《文物》1993年第4期,頁18-28。
[11]陳松長,《馬王堆漢墓帛畫“太一將行”圖淺論》,《美術史論》1992年第3期,頁90-96;陳松長,《馬王堆帛畫“神祇圖”辨証》,《江漢考古》,1993年第1期,收入陳松長,《簡帛研究文稿》(北京:綫裝書局,2008),頁308-317。
[12]胡文輝,《荊門“辟兵”戈考述──一個學術史個案》,《學人》第7輯(1995),頁303-323;胡文輝,《馬王堆〈太一出行圖〉與秦簡〈日書·出邦門〉》,收入胡文輝,《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叢考》(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頁145-158。
[13]後來黃盛璋也指出這一點,見黃盛璋,《論“兵避太歲”戈與“太一避兵圖”爭論的癥結、引出問題是非檢驗與其正解》,《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10輯(2003),頁17-34。
[14]饒宗頤,《圖詩與辭賦—馬王堆新出〈太一將行圖〉私見》,湖南省博物館編,《湖南省博物館四十周年紀念文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頁79-82。
[15]李建毛,《馬王堆漢墓“神祇圖”與原始護身符籙》,《馬王堆漢墓研究論文集》(長沙:湖南出版社,1994)。
[16]連劭名,《馬王堆帛畫〈太一避兵圖〉與南方楚墓中的鎭墓神》, 《南方文物》1997年第2期,頁109-110。
[17]楊琳,《馬王堆帛畫〈社神護魂圖〉闡釋》,《考古與文物》2000年第2期,頁71-75。
[18]黃盛璋,《論“兵避太歲”戈與“太一避兵圖”爭論的癥結、引出問題是非檢驗與其正解》, 頁17-34;黃盛璋,《長沙馬王堆出簡、帛文書、畫、圖與楚文明發展重要貢獻舉要》,收入黃盛璋主編,《亞洲文明》(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第四集,頁114。
[19]邢義田,《太一生水、太一出行與太一坐:讀郭店簡、馬王堆帛畫和定邊、靖邊漢墓壁畫的聯想》,《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30期(2011),頁1-34,參見頁8,注18。
[20]李淞,《依據疊印痕跡尋證馬王堆3號漢墓〈“太一將行”圖〉》,《美術研究》2009年第2期,頁44-50。
[21]《中國考古文物之美·輝煌不朽漢珍寳·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光復書局,1994),圖版8。
[22]李淞,《依據疊印痕跡尋證馬王堆3號漢墓〈“太一將行”圖〉》,頁49。
[23]陳斯鵬,《戰國秦漢簡帛中的祝禱文》,收入陳斯鵬,《簡帛文獻與文學論考》(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頁110-131。
[24]胡文輝,《馬王堆〈太一出行圖〉與秦簡〈日書•出邦門〉》,頁145-158。
[25]這裡的“祝”也相當於後世的“咒”或“咒語”(incantation)。陳思鵬以爲後世的“咒語”是“特指巫師口訣的,普通人念念辟災祈福的言語,似乎不宜叫做‘咒’”,但事實上,像《太一祝》這樣的咒語,並不是一般的“辟災祈福的言語”(這一類言語應該叫“禱”),而是伴隨一定的儀禮動作,其本身就具備魔力的言語。先秦和漢初的祝禱文基本上都是普通人自己念的,這是戰國時期發展起來的日常宗教的一個顯著特徵。陳斯鵬,《戰國秦漢簡帛中的祝禱文》,頁123-124;來國龍,《論楚卜筮祭禱簡中的“與禱”》,《簡帛》第6輯(2011),頁359-378,特別是頁374,注1。
[26]來國龍,《戰國秦漢“冥界之旅”新探:以墓葬文書、隨葬行器及出行禮儀為中心》,收入馮天瑜主編,《人文論叢(2009年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頁156-157。
[27]呂亞虎,《戰國秦漢簡帛文獻所見巫術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頁244-247。
[28]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39-40。
[29]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頁139。
[30]胡平生、張德芳編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182。
[31]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圖版頁127,註釋頁240。原圖版一〇七貳,註釋文字說“本簡此段雙行書”,但細審圖版此段下部並為雙行書。整理小組的註釋不知何據。
[32]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頁288-289,354-355;胡文輝,《馬王堆〈太一出行圖〉與秦簡〈日書•出邦門〉》,頁151。
[33]李家浩指出,“將(?)承弓”可能是古書上提到的請戰前授弓矢、操弓射矢的儀式有關,見李家浩:《論〈太一避兵圖〉》,頁282。
[34]“包”(抱)是古代占測凶吉時形容雲氣形狀的專門術語,“赤包白包”乃指兩种不祥的雲氣。類似“包”字又見馬王堆其他帛書,討論見陳松長,《馬王堆帛畫“神祇圖”辨証》,頁312-313。
[35]李零補“傷”字,陳松長補“當”字。因此句的主語是“百兵”,筆者以爲補“傷”字較妥。
[36]“唾”的解釋,參見陳松長,《馬王堆帛畫“神祇圖”辨証》,頁313。
[37]太一頭像題記的上方似乎還有文字殘跡,但是已經無法辨識。最近黄儒宣在《馬王堆〈辟兵圖〉研究》一文,重申該圖爲《辟兵圖》的論證。她的主要依據是“發現一處長期被忽視的字跡,用作解開中央主神身份的關鍵鑰匙”。作者所謂的“關鍵鑰匙”是帛圖中心人物上方的一處字跡,她認爲是“蚩尤”兩字:“首字上半疑爲‘出’,下從‘虫’,以‘出’爲聲符,讀爲‘蚩’。”作者认爲“蚩”與“出”兩者聲母相同,韻部輾轉通假,“物部與職部有通假之例”,“職部是之部的入聲”,因而得出“物部或可與之部通假”;最後又補一句“又或此字上半所從就是‘之’字”。關於第二個字,作者説“次字僅存上方部分筆畫,無法確定爲何字”。今按:作者推測為“蚩尤”的字跡完全不能落實。不但第二個字無法確定,就是第一個字也不能確定,加之轉輾通假更是無根之談。黄文刊臺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5本第2分(2014),頁167-207。
[38]李家浩以古代“夷”(B-S*ləj)、“弟”(B-S*lˤəjʔ)二字形音皆近,認爲“武弟子”即“武夷子”,可備一說。見李家浩,《論〈太一避兵圖〉》,頁285。
[39]虒,《說文解字》:“委虒,虎之有角者也。”段玉裁注:“虎無角,故言有以別之。”參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211。帛圖上的形象,頭戴獨角帽,身著緊身的裘衣,可能即指有角的虎皮裘衣。
[40]學者已經指出,這裡指的是青龍與黃龍參與冶鑄、製造兵器(或銷熔兵器)的一種方術。這兩段題記文字可以和《越絕書》中有關文字相比較。《越絕書》卷第十一〈越絕外傳記寶劍第十三〉:“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爐,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見李步嘉,《越絕書校釋》(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頁266。李家浩指出題記中的“容(鎔)”是指鑄器之模範,因此這兩段題記應該是跟冶鑄兵器有關的一種數術,見李家浩,《再論“避兵太歲”戈》,頁32。金正耀則認爲“容(鎔)”是指“鎔罐”,帛圖裡的“鎔”與“爐”是與銷熔敵方兵器有關的一種避兵方術,見金正耀,《鎔字古義鈎沉—兼論帛書辟兵圖的文化記憶》,收入張光裕、黃德寬主編,《古文字學論稿》(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頁 472-477。
[41]周世榮,《馬王堆漢墓的“神祇圖”帛畫》,頁926。
[42]李學勤,《“兵避太歲戈”新證》,頁35-39。
[43]胡文輝,《馬王堆〈太一出行圖〉與秦簡〈日書•出邦門〉》,頁153-154。
[44]林巳奈夫,《饕餮=帝說補論》,《史林》1993年第76卷,第5號,頁78-118。
[45]姚周輝,《神秘的幻術:降神附體風俗探究》(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3);Edward L. Davis, 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 (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尤其是頁1-20有關“憑依”和“spirit-possession”的討論。當然,從史前到近現代,“降神附體”的觀念也隨著中國社會與宗教的演變而變化。
[46]《禮記·曾子問》:“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于同姓可也。”見王文錦,《禮記譯解》(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263。
[47]《左傳·僖公五年》:“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參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309-310。
[48]《左傳·昭公七年》:“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1292。
[49]《左傳·昭公八年》:“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1300。
[50]Michael J. Puett, To Become a God: Cosmology, Sacrifice, and Self-Divinization in Earl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n Center for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2002;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Review of To Become a God: Cosmology, Sacrifice, and Self-Divinization in Early China, by Michael J. Puett.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4.3 (2004): 465-479.
[51]金開誠、董洪利、高路明校注,《屈原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704-718。
[52]《韓非子》校注小組編寫、周勛初修訂,《韓非子校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頁69。
[53]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8-9.
[54]蔡邕著,鄧安生編,《蔡邕集編年校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235。
[55]出行者通過巫術動作而爲神靈所附、變化身份,這與後世道教的“變神”、“變身”類似。關於道教的“變身”、“變神”,參看Paul Anderson, “Bianshen, 變身 or 變神 ‘transformation of the body’ or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irit’,” in The Encyclopedia of Taoism, ed. Fabrizio Pregadio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1: pp. 230-231.
[56]Jan N. Bremmer, “Don’t Look Back: From the Wife of Lot to Orpheus and Eurydice,” in his Greek Religion and Culture, the Bible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Leiden: Brill 2008), pp. 117-132.
[57]Jan N. Bremmer, “Don’t Look Back: From the Wife of Lot to Orpheus and Eurydice,” pp.125-126.
[58]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頁67。
[59]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744。
[60]程樹德,《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729-730。
[61]程樹德,《論語集釋》,頁730。
[62]楊樹達,《論語疏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頁160。
[63]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741-742。
[64]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頁200。
[65]呂亞虎,《戰國秦漢簡帛文獻所見巫術研究》,頁245。
[66]吉川忠夫、麥谷邦夫編,朱越利譯,《真誥校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287-288;吉川忠夫,《淨室考》,收入劉俊文主編,許洋主等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446-477,特別是457-458。
[67]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頁157。
[68]組纓,是指以組帶作的冠繫。陳偉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頁124。
[69]劉信芳讀為“襗”。《說文解字》:“襗,绔也”;“绔,脛衣也”,也就是褲子。這裡的“狐襗”可能是指以狐皮做成的褲子。參見陳偉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頁124-125。
[70]陳偉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頁119。
[71]陳偉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頁290。
[72]Anneliese Bulling,“Notes on Two Unicorns,” Oriental Art, 3 (1966), pp. 109—113;圖像參見Annette L. Juliano and Judith A. Lerner, Monks and Merchants: Silk Road Treasures from Northwest China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Inc., with The Asia Society, 2001), pp. 44—46.
[73]林巳奈夫,《漢代男子のかぶりもの》,《史林》1963年第46卷,第5號,頁80—126;孙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説》(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236。
[74]關於鹿角,參見Xiaoneng Yang, ed.,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Archaeology: Celebrated Discoverie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Kansas: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1999),p. 338.
[75]關於戰國時期把死亡看作是一種出行的論證,參見來國龍,《戰國秦漢“冥界之旅”新探:以墓葬文書、隨葬行器及出行禮儀為中心》,頁156-157。
[76]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原始社會至南北朝繪畫》(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7),頁43-45。
[77]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原始社會至戰國雕塑》(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7),頁117。
[78]Kwang-chih Chang,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176; David N. Keightley, “Shamanism, Death and the Ancestors: Religious Mediation in Neolithic and Shang China (ca. 5000-1000 BC),” Asiatische Studien 52.3 (1998): pp. 763-831;黃銘崇,《“饕餮紋”的再思考:一個方法的省思》,《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32期(2013),頁1-102。
[79]Michael Loewe, “Man and Beast: The Hybrid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Literature,” in Michael Loewe, Divination, Mythology and Monarchy in Ha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8-54.
[80]Alain Thote, “Au-delà du monde connu: représenter les dieux,” Arts asiatiques 61 (2006) : 57-74.
[81]Poo, Mu-chou, In Search of Personal Welfare: A View of Ancient Chinese Relig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8), p. 95.
[82]Alfred Salmony. Antler and Tongue: An Essay on Ancient Chinese Symbolism and Its Implications. Artibus Asiae, supplementum 13 (Ascona, Switzerland: Artibus Asiae Publishers, 1954).
[83]Reviews by Basil Gray,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97. 628 (1955), 232-233; by Robert Heine-Gelden, Artibus Asiae, 18.1 (1955), pp. 85-90; by L. Lanciotti, East and West, 51(1955), p. 63; by J. Průsěk Archiv Orientální, 25.3 (1957), p. 511; and Alfred Salmony. “With Antler and Tongue.” Artibus Asiae, 21.1 (1958), pp. 29-36.
[84]Marjorie Garber and Nancy J. Vickers, eds. The Medusa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85]Sigmund Freud, “Medusa’s Head,” in Sigmund Freud, edited by Werner Hamacher and David Wellbery. Writings on Art and Literature (Stanford: Stanfoe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64-265.
[86]W. J. T. Mitchell, Picture Theory: Essays on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78-80.
[87]Thomas Alberecht, The Medusa Effect: Representation and Epistemology in Victorian Aesthetic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9); Roger Caillois, The Mask of the Medusa, trans. George Ordish (New York, C.N. Potter 1964).
[88]E. H. Gombrich, The Sense of Order: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Decorative Art (London: Phaidon Press Limited, 1984), pp. 272-281.
[89]Joseph E. LeDoux, “Emotion, Memory and the Brain.” Scientific American 270.6 (1994), pp. 32-39。
[90]Guolong Lai, Excavating the Afterlife: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Chinese Religion (Seattle: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forthcoming 2015), chapter 1.
[91]康豹,《染血的山谷──日治時期的噍吧哖事件》(臺北:三民書局,2006)。
© Copyright 2005-2021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