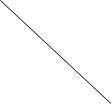金文札記之二
作者:薛培武 發布時間:2018-08-31 08:39:30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2015届碩士研究生)
(首發)
一、簡釋師 鼎中的“禰宗”
鼎中的“禰宗”
師

鼎于1974年出土于陝西省扶風縣法門鎮強家村一青銅器窖藏,該器著錄于《集成》02830號,我們在讀過該銘之後,對銘文最後一部分有一點不成熟的想法,現簡單的寫出來。其最後一部分銘文如下(釋文用寬式):

敢對揚王休,用綏,乍公上父尊于朕考郭季易父

宗。
學者一般都將“

”隸定為“

”
[1],據筆者所見,唯《新金文編》將其隸為“

”
[2],《商周金文摹釋總集》將其摹作“

”,釋作“

”
[3],從這裡可以看出一些字編、著錄書等并不是沒有注意到“

”字左上的“止”形,只是在釋寫的時候,將其與“

”認同。該字左上從“止”是比較明顯的,顯然不能與“

”對等,《新金文編》的隸定可從。
再分析這個字形之前,我們先來看這個字在銘文中的用法。于豪亮先生認為“

”乃器主之父郭季易父的名,與“易父”之“易”代表的詞“逷”,名字相因
[4]。這種直呼其父之名的做法,顯然有悖於青銅器銘文的常例,于先生的這種理解顯不可從。《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將“

宗”括讀為“秩宗”,說:“《說文·辵部》達,行不相遇也。從辵幸聲,《詩》曰‘挑兮達兮’,达,達或從大,或曰迭。《尚書·舜典》‘俞!咨伯,汝作秩宗’”,并解釋說“秩宗”指“宗廟之有秩序”,“故秩宗也是泛指宗廟”
[5]。先不論其在字形說解上的謬誤,就連所舉文獻中作為官名的“秩宗”,也不能跟其所做出的解釋相合,此說有很多需要商榷之處,顯不可從。
從金文的常例來看,“

宗”應該是一種宗廟的稱呼,從整句話所述來看,這個宗廟最可能是其考“郭易父”所屬。前引于豪亮先生解釋“乍公上父尊于朕考郭易父宗”這句話說“作了一件祭祀他祖父公上父的祭器,放在他父親的宗廟裡”,對相關銘文的內容理解是正確的。
古代稱奉祀亡父的宗廟為“禰”,《公羊傳》隱公元年:“惠公者何,隱公之考也。”何休注:“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禰。”有單言“禰”者,《周禮·春官·甸祝》“舍奠於祖廟,禰亦如之”,鄭玄注:“禰,父廟。”《漢書·韋賢傳》:“既去禰祖,惟懷惟顧。”顏師古注:“父廟曰禰。”亦有言“禰廟”者,如《左傳》襄公十二年:“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我們知道,“宗”本為祖先宗廟建築群體,或祭祀自然神祗的場所。既有集合宗廟的“宗”,也有單獨奉祀某一位祖先的“宗”。“

宗”顯然與“禰廟”相關。我們再來分析字形,

字右邊所從偏旁即見于甲骨文中的“逸”,茲舉例如下(字形取自《新甲骨文編》第574頁):



趙平安先生首先根據楚簡的材料,將其準確的釋讀為“逸”
[6],得到學者的普遍接受。所以,該字從

從攵,并且以

(逸)為聲符。進而,我們認為這個字有兩種分析方法,一種想法是認為他是“抶”字的異體,另一種意見我們根據從“㚔”的字加“攵”與不加“攵”互見這樣的現象(如“執”、“盩”等),認為這個字有可能就是“

”(逸)的繁體。我們認為“

”可直接讀為“禰”。上舉甲骨文中的“逸”還有下面一種異體(見《新甲骨文編》第573-574頁):



前此學者多將這類形體直接看作“

”的省體,王子揚先生指出這類的“

”應當分析為從“止”“埶”省聲
[7],此說可從。殷墟甲骨文中的“埶”,常表示遠邇之“邇”
[8]。所以“

”聲自可與“爾”聲通,則“

”可讀為“禰”。
綜上,我們認為“

宗”應該讀為“禰宗”,不僅于文意為勝,在字形上也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二、虢叔旅鐘“列御”淺解
虢叔旅鐘著錄于《集成》00238-00244號,其銘曰(寬式釋文):
虢叔旅曰:“丕顯黃考惠叔,穆穆秉元明德,御于厥辟,

純亡愍。旅敢肇率型皇考威儀,△御于天子,卣(攸)天子多賜魯休,旅對天子魯休揚……。”
我們著重討論銘文中的“△”,“△”字結構不好辨認,加之拓本不甚清楚,難以準確釋讀,所以,一般都將該字存疑,或者釋讀為“淄”,括讀為“祗”
[9],後者是將其認作金文中的“

”,是很有啟發性的意見。首先需要交代的是,虢叔旅鐘一件現藏故宮博物院,一件現藏上海博物館,兩件現藏日本,一件現藏不明只有拓本(如下圖3)。我們先把《集成》該組器物的“△”字拓片和較清晰的照片列在下表,以備說解。
其中的照片,圖1選自《故宮青銅器圖典》第109頁,圖2、4、5選自《陝西金文集成》。根據照片,“△”字上部似乎較為清楚,一般作“

”形,中間由於殘泐不清,不好辨認,有可能是從“水”作,不過,至少能顯示出一個“

”形。下部形體較混亂,圖1-4最下面從“几”,“几”形与“

”形之间是否还有一个“几”,还不能确定,不过图1清楚的顯示了中間確實可能還有一個“几”。圖5,從拓本和影像看,下部有可能也是“

”形而未畫全者。我們認為,如果從整體著眼的話,與這個字最接近的,就是金文中常見的“

”,“

”字下部有從兩個“几”形的情況,可與圖1中“△”參看(參下引吳師文)。前面提到學者將其與“

”聯繫的觀點確實值得考慮,不過學者對“

”字本身的分析卻是有很大問題的。目前來看,“

”字以吳振武師的分析最為可信
[10]。吳振武師將“

”字釋讀為“瀝”,并認為其中的“鬲”字表音,這是正確的。所以,“△”也當從“鬲”聲出發考慮其音讀,我們認為“△”可讀為“列”,訓為“列位”,“列御”即“列位”于天子臣屬,服御于天子。
本條札記是兩年前的舊想法,曾向蔣玉斌先生請教,蔣先生告知程鵬萬先生有一篇未刊稿將之釋為“再”。因為並未看過程先生的文章,所以對程說不好評議。讀為“再”的話,有一個缺陷,即“再”解釋為“第二次”的意思,一般都是針對同一個主體而言。蔣先生亦向我指出這個疑慮,存此備考。
附記:第一條寫完后,曾向滕勝霖、陳小龍、王森、馬超諸位兄長求證,得到他們的支持,又得到簡帛網編輯先生的一些建議,一併致謝。
[1] 最近出版的《陝西金文集成》也徑將其隸為“

”(張天恩主編:《陝西金文集成·寶雞卷·扶風》,三秦出版社,2016年,第69頁)。
[2] 董蓮池:《新金文編》,作家出版社,2011年,第397頁。
[3] 張桂光主編:《商周金文摹釋總集》,中華書局,2010年,第437頁。
[4] 于豪亮:《陝西扶風縣出土虢季家族銅器銘文考釋》,載《于豪亮學術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45頁。
[5] 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卷·商、西周青銅器銘文釋文及注釋》,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36頁。
[6] 趙平安:《戰國文字的“

”與甲骨文的“

”為一字說》,載《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商務印書館,2009年。
[7] 王子揚:《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中西書局,2013年,第247-248頁。
[8] 裘錫圭:《釋殷墟甲骨文裡的“遠”“

”(邇)及有關諸字》,《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9] 《殷周金文集成》釋文如此括注,《銘圖》等從之。
[10] 吳振武:《釋

》,《文物研究》總第六輯,黃山書社,1990年。又參謝明文:《競之

鼎考釋》,《出土文獻》第9輯,中西書局,2016年10月,第68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為2018年8月31日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