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越木簡校釋五則
作者:林嵐 發布時間:2023-09-30 09:13:24(首發)
2022年,《南越木簡》一書出版,公佈了南越國宮署遺址滲水井J264所出木簡的釋文與圖版。[1]對於此批材料,學界已有不少考釋成果,我們在此基礎上對其中的一些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敬請方家指正。
簡12與簡15中出現了2例被整理者解釋爲人名的“![]() (遲)”字,《南越木簡研究》中釋爲“菌”“
(遲)”字,《南越木簡研究》中釋爲“菌”“![]() ”。[2]按,兩字字形分別作[4]、[5],整理者已指出,該字見於睡虎地秦簡。睡虎地秦簡中該字作[6],睡虎地秦簡整理者已改釋爲“蓾”,讀作“虜”。[3]南越中的2例亦當改釋爲“蓾”,在簡文中用作人名,可不讀。
”。[2]按,兩字字形分別作[4]、[5],整理者已指出,該字見於睡虎地秦簡。睡虎地秦簡中該字作[6],睡虎地秦簡整理者已改釋爲“蓾”,讀作“虜”。[3]南越中的2例亦當改釋爲“蓾”,在簡文中用作人名,可不讀。
“蓾”字在秦及西漢早期多見,目前共有12例。從寫法上看,所從的“鹵”主要有兩種形體,一是鹵上部一橫筆超出豎筆,如[7]、[8];二是寫作完全封閉的囗形,如[9]、[10]。從分佈情況上看,兩種形體未見有明顯的時代差異,秦簡及西漢早期簡牘中兩種形體都有使用。但在同一批簡牘中的寫法較統一,應與地域和書手習慣有關。先秦古文字中“鹵”象盛鹽鹵器之形,[4]如免盤(《殷周金文集成10161》)字作![]() 。第一類形體即是古文字字形外部筆畫的平直化,其上略突出的筆畫演變成爲超過囗形的橫筆。趙平安先生認爲,戰國時期,從鹵之字的外部筆畫已出現完全封閉的形體。[5]秦漢時期“蓾”字所從之鹵的第二類形體可以看作由此演化而來。
。第一類形體即是古文字字形外部筆畫的平直化,其上略突出的筆畫演變成爲超過囗形的橫筆。趙平安先生認爲,戰國時期,從鹵之字的外部筆畫已出現完全封閉的形體。[5]秦漢時期“蓾”字所從之鹵的第二類形體可以看作由此演化而來。

| 
| 
| 
| 
| 
| 
|
| 南越12 | 南越15 | 睡虎地《封診式》36 | 嶽麓伍149 | 張家山《二年律令》436 | 里耶貳557 | 虎溪山《閻昭》下50 |
| [4] | [5] | [6] | [7] | [8] | [9] | [10] |
簡17整理者釋文作:王所財(賜)泰(太)子今案齒十一歲高六尺一寸身[完]毋豤傷
其中“財”字,整理者注:“與馬王堆帛書《老子(甲)》的‘財’字相似。疑爲‘賜’字之誤。”[6]姚磊先生據整理者說,將“財”讀爲“裁”。[7]
按,該字作[11],馬王堆帛書中“財”字作[12]。秦及西漢早期,“財”字所從才多寫作十字形下加一點。從南越木簡整理者給出的紅外綫圖版上可以看見,所謂“才”的橫筆上方仍有兩小橫,且其中部雖漫漶,但右側仍有墨跡。我們認爲,該字應是從昜的“賜”字。
秦漢簡中,這類寫法的“賜”字很常見,如[13]、[14],《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全編》中認爲,這類從昜之字爲“賜”字訛體。[8]秦漢簡帛中“易”“昜”在獨立成字或作爲構件時常見互作,尤以“易”與所從之字作“昜”者爲多,嶽麓秦簡11例“易”字皆寫作“昜”形,如[15]。秦及西漢早期,從昜之字寫作從易者較少見,有些昜字形的橫與上部共用,且寫得較短,看上去與易的差別很小,如[16];但也有些字形徑作易,如[17]。西漢中晚期時,由於書寫上的簡便,有些從昜之字的一橫會被省去,如[18]、[19]、[20]。這類字形若再進一步草化上部的日形,即與簡體之????沒有什麼區別,如[21]、[22]。

| 
| 
| 
|
| 南越17 | 馬王堆《老子甲本》146 | 嶽麓伍327 | 馬王堆《戰國縱橫家書》40 |
| [11] | [12] | [13] | [14] |

| 
| 
| 
|
| 嶽麓陸151 | 馬王堆《相馬經》53上 | 馬王堆《老子甲本》82 | 居延新簡EPT51:374 |
| [15] | [16] | [17] | [18] |

| 
| 
| 
|
| 居延漢簡136.3 | 肩水金關T24:574 | 肩水金關T24:416A | 居延新簡EPT50:17 |
| [19] | [20] | [21] | [22] |
簡47中有兩個用作人名之字,整理者釋爲“最”,字形作[23]、[24]。《說文•冃部》:“最,犯而取也。从冃从取。”又《說文•冖部》:“冣,積也。从冖,从取,取亦聲。”段玉裁在“最”字條下注:“冣之字訓積,最之字訓犯取。二字義殊而音亦殊。”“最”“冣”二字的小篆字形僅“取”字上是否有兩橫的區別,在秦漢簡的實際使用上,二者的區別更小,有時甚至在字形上看不出差異。例如,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中5貳之字作[25],表示聚義;簡15背壹之字作[26],表示最義,兩字皆寫作從宀從一從取,在字形上沒有差別。馬王堆帛書中,“冣”“最”皆有寫作從宀從取之形者。[9]對此,《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全編》指出:“冣……‘最’字或訛作與之同形。”[10]由於南越該簡兩字爲同一人名,意義難定,我們認爲,宜從字形上釋爲“冣”。相似的情況見於鳳凰山漢簡九號墓19,該字作[27],亦爲人名,鳳凰山漢簡整理者釋文作:“大奴冣”。[11]若需嚴格隸定,可作“![]() ”,看作“冣”字異體。秦漢時期從冖之字常寫作從宀,如“冠”字,秦漢簡中多寫作“
”,看作“冣”字異體。秦漢時期從冖之字常寫作從宀,如“冠”字,秦漢簡中多寫作“![]() ”。
”。

| 
| 
| 
| |
| [23] | [24] | [25] | [26] | [27] |
簡85整理者釋文作:陽□[汜]見人迹可□三百人之
其中,“可”下一未釋字作[28],該字圖版右下角有一墨跡,我們認爲當是勾識符號,該字即“二”字。《南越木簡研究》中將該簡斷句作:“陽□□見人迹,可□三百人,之”,[12]當可從。整理者注:“可:爲約計詞,意爲大約”,[13]“可二三百人”,即大約二三百人之意。該簡當斷作“陽□[汜]見人迹,可二三百人,之”。
在西北簡中,書寫兩個連續的數字,尤其是僅有橫畫的字時,中間常加上勾識符號,如[29]、[30]。李均明先生曾指出:“由於簡牘文字爲豎寫,而數詞一、二、三爲橫劃,假如一、二之間不加句讀符,則易誤認做三……因此,有關數詞之句讀符,最常施於一、二、三之間”。[14]對於這類符號的性質,雖然學者們有不同意見,[15]但皆認可其加在兩個數字之間防止誤識的作用。南越簡中此例亦當與西北簡的勾識符號作用相同。此前討論這類符號時,多集中於西漢中晚期的西北簡中,南越簡此例說明西漢早期南越地區已見此種符號的用法。若進一步上溯,可見里耶秦簡中已有使用,見[31]。
在連續的橫畫數字中,除了使用勾識符號隔開外,有時還會有意改字。例如,北大秦簡《算書》甲種《里田術》(簡81、96):“里田述(術)曰:里乘里,一殹(也),見一鼠(予)二,見二鼠(予)四,四者加一,因而三之,即頃畮(畝)殹(也)。其一述(術)曰:里乘里,里殹(也),壹(一)參(三)之,有(又)參(三)五之,即頃畮(畝)數殹(也)。”同爲此術,張家山漢簡《算數書》187-189作:“里田术(術)曰:里乘里,里也,廣、從(縱)各一里,即直(置)一因而三之,有(又)三五之,即爲田三頃七十五畝。其廣從(縱)不等者,先以里相乘,巳(已)乃因而三之,有(又)三五之,乃成。今有廣二百廿里,從(縱)三百五十里,爲田廿八萬八千七百五十頃。直(置)提封以此爲之。一曰:里而乘里,里也,壹(一)三而三五之,即頃畝數也。”這兩篇《里田術》中,“一”“壹”並見使用,但在與“三”連寫時,皆用“壹”。北大秦簡中,甚至將與“一”連寫的“三”也改作“參”,並影響到後文與“五”連寫之字亦作“參”。西北簡中有部分記錄乘法口訣的簡,在“一二而二”“二三而六”一句中,“而”字前的“二”“三”常寫得很小,在前一字的右下角,如[32]、[33]。這種縮小的寫法,一方面是應是爲了與上文使用重文符號的句子保持格式和間距的相對一致,如“六=卅六”作[34];另一方面應當也是爲了避免誤認。
 
| 
| 
| |
| 南越85 | 敦煌馬圈灣7A | 肩水金關T23:704 | |
| [28] | [29] | [30]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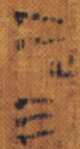
|  
| 
| 
|
| 里耶12層2130B | 肩水金關T26:5A | 敦煌馬圈灣1062 | 肩水金關T26:5A |
| [31] | [32] | [33] | [34] |
簡158整理者釋文作:□百□六十人![]()
第一個未釋字作[35],將紅外圖版與彩色照片對照,可以看出該字中部爲一交叉筆畫。我們認爲,該字即“五”。從文意上看,該簡是對人數的統計,“百”上爲一數詞很合理。從字形上看,南越簡中一般的“五”字作[36],兩相比較,簡158之字向右的點劃上下皆有曲筆。這應是早期隸書的一種寫法,如[37]、[38],能看出明顯的曲筆。這一筆畫與最上一橫相連處容易斷開,向下的曲筆若同時寫得不夠圓潤,如[39],看上去即與成熟的隸書之“五”字沒有很大區別。
 
|  
| |
| 南越158 | 南越81 | |
| [35] | [36] | |

| 
| 
|
|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22 | 馬王堆《周易》58 | 馬王堆《周易》36 |
| [37] | [38] | [39] |
[1]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博物院:《南越木簡》,文物出版社,2022年。
[2]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博物院編著:《南越木簡》,第133頁。
[3] 陳偉主編,彭浩、劉樂賢等撰著:《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壹、貳),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79頁。
[4] 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1568頁。另有學者認爲還有一類更爲複雜的“鹵”字。參見劉洪濤:《釋????——兼談“????”字的不同來源》,《“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9本第2分),2018年,第247-277頁。
[5] 戰國時期這類形體還省去內部的四點。詳見趙平安:《戰國文字中的鹽字及相關問題研究》,《考古》,2004年第8期。
[6]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博物院編著:《南越木簡》,第54頁。
[7] 姚磊:《讀〈南越木簡〉札記(三)》,武漢大學簡帛網,2023年5月23日。
[8] 劉釗主編:《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全編》,2020年,中華書局,第739頁。
[9] 參看劉釗主編:《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全編》,第869、871頁。
[10] 劉釗主編:《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全編》,第869頁。
[1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鳳凰山西漢簡牘》,中華書局,2012年,第66頁。
[12]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博物院編著:《南越木簡》,第128頁。
[13]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博物院編著:《南越木簡》,第72頁。
[14] 李均明:《簡牘符號考述》,《華學》(第2輯),中山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93-107頁。
[15] 如馬怡先生認爲其爲鉤識符,將兩字分開以免誤認;尚穎先生認爲其表示間隔,用法等同於今天的頓號;王錦城先生認爲其加在“一二”之間,主要是爲了防止誤認。詳見馬怡:《〈趙憲借襦書〉與〈趙君????存物書〉》,《簡牘學研究》(第5輯),甘肅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頁;尚穎:《〈肩水金關漢簡(1-2)〉所見各類符號及其作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5年1月11日;王錦城:《西北漢簡字詞雜考四則》,《簡帛》(第18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39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23年9月27日1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