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国及秦汉时代官方“受錢”制度和质钱
作者:柿沼陽平 發布時間:2009-06-26 00:00:00(早稻田大學文學研究系)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2009提交論文首發)
序到目前,报告者对中国古代货币经济的开展过程及其特性进行了研究[1]。结果发现所谓的货币经济兴起于战国乃至秦汉时期,其中的秦汉政府对当时的主要货币(经济领域的流通手段)——钱·黄金·布匹进行了统一管理,并且试图利用它们对人民进行更有效的控制。
特别是其中的钱,因其能够体现零碎的商品价格并且在材料上也具有便于保存的优势,所以在战国时代中期之后,便被选定为国家的结算手段受到统一管理。也就是说,秦汉政府将物价划分为固定官价、平贾和实势价格三个等级,并使钱作为其中最基本的价值衡量标准,不管半两钱大小重量的差异,均视为同一面额,并只让其在国内流通,然后依据其枚数的总和对决定商品价格的衡量体制进行调整。而与此相对,在民间由于钱与钱之间的重量差别问题十分突出,因此在最初这个政策似乎并未被贯彻执行下去,直到西汉武帝时,由于中央政府专门铸造了“五铢钱”,而暂时安定并被逐渐接受。此后,钱作为国家物资流通的润滑剂开始发挥其功效。
但是,为了使以钱为媒介的国家物资流通能够安定且持久的发挥其机能,除了使国家的钱流向民间之外,还必须使民间的钱再回流至国家,否则,就会导致秦汉政府的国库迅速走向枯竭。因此,由官吏进行的“受錢”(接受纳税的钱或根据买卖所得的钱)就变得非常重要。那么,这究竟是按照一种什么样的程序来执行的呢。如其具体手续较为模糊的话,在其中就容易出现一些不正当的行为,长此以往,人民对政府也就失去了信任感。因此,对于“受錢”手续的要求理应十分严格。在本报告中先以官吏在“市”里的“受錢”手续为例,对这项制度的一面进行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讨论当时的国家政府对“受錢”的重视程度,并且结合一些乍一看似乎与之相矛盾的事例,通过对两者的分析阐述国家在支配方面的实际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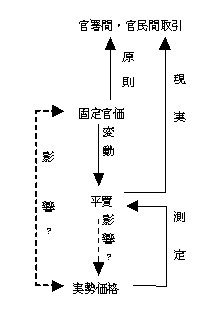
〔圖1〕漢代的物価制度
1.战国时秦的“市”里的“受錢”众所周知,在战国与秦汉政府的所谓“受錢”中存在有若干种项目,在战国时秦的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里,特别记载有“市”里的官吏在进行“受錢”时的程序。
A.爲作務及官府市受錢必輒入其錢缿中令市者見其入不從令者貲一甲。關市(関市律164)。
对于其中「爲作務及官府市受錢」的解读方法有四种说法。
①从事作务者和从事商业活动的官员接受钱的场合
②进行作务并于官府的市接受钱的场合[2]
③进行作务及官府的买卖时接受钱的场合[3]
④为作务及官府进行商业交易的时候接受钱的场合[4]
但是,如果将本条前半部与后面的《二年律令》金布律(429)的前半部进行相对照的话即:
<秦律> 爲作務及官府市 受錢
<汉律> 官爲作務 市及受租質錢
可以得知两者所表达的内容是类似的。因此,参照秦律对汉律进行解读的话,在秦律中“爲作務”和“官府市”被“及”字断开,由于“官府市”不会被解读为“进行作务”的场所,所以在汉律中出现的“市”同样也不应该是“进行作务”的场所。由此可知,汉律中的“官爲作務市”并非“在市进行官的作务”而应该解读为“进行作务·市的官员”或“进行作务的官员及从事商业活动者”。因此,秦律中的“作務”和“官府市”应是并列关系,“官府市”并不是指“受錢”的场所。可知②是不成立的。下面的④中的“爲”被解读为“为了”,持此论者又进而使用汉律解读为“官为了进行作务而进行商业活动的场合及接受租·质钱的场合”,但是如果按照这样进行解读的话,在秦律中就成了为了“作务及官府”,汉律中则是为了“作务”,也就是说各自都被假设为进行“市”(商业交易)的场合,在两者的内容中也就产生了差异,而且按照④的说法,汉律中的主语就成了“官”,而在秦律中则没有了主语,文中的意思不通。所以,我认为①和③的解读方法才是妥当的。这样一来,不论是按照①还是③,原句的意思都为“从事手工业以及官府所属的人进行商业交易这一行为”或解释为“从事手工业的人以及进行商业交易的官府所属的人(官吏)”。
那么,“作务(者)”和“在官府管理下从事商业交易(者)”各自代表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说前者可以解释为从事手工业[5],或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及制作工作等[6]。但是为何“作務”和“受錢”有着直接关联则不太清楚,根据《太平御览》卷627賦斂中所引的恒谭《新论》中的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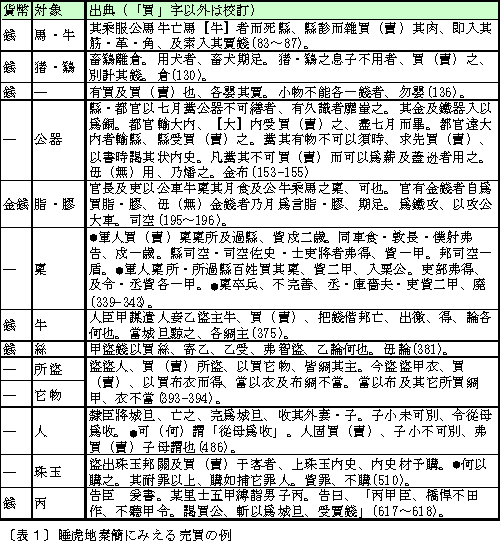
可以得知“作務”也担负着帝室的财政收入。由此,史料A中的“作務”不仅仅指从事手工业活动,也应该参与了经济活动。关于下面的“在官府管理下从事商业交易(者)”在睡虎地秦简中的其它几处也能零散的看到官吏进行交易的实际事例的记载(表1)。因此可知,史料A中的“官府市”应是指从事商业交易的官吏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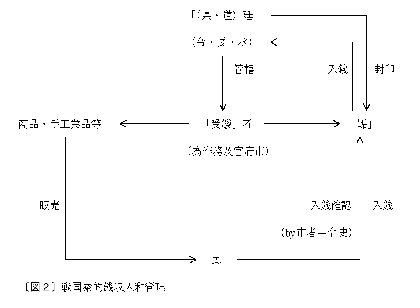
①让支付方对其进行确认[7]。
②让受领方确认钱已被装入[8]。
③在申告纳税的时候给市吏展示其所得金额[9]。
然而,按照②的说法,“受錢”者自己“见其入”,也就是说,在这里 “受錢”者是将钱放入“缿”内的动作主体,而并非使令句“让其确认钱已被装入”的对象,与此相对,①的说法则是:“为了使双方之间彼此不产生不正当行为和误解,规定由官方的‘受錢’者让支付方确认钱已被装入”,从内容上来看这种说法应没有什么问题。另外,③将本条与纳税规定进行挂钩虽然缺乏论据,但是在“市者=市吏”这点上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据岳麓书院收藏的秦简[10]:
C.關市律曰、「縣官有賣買也、必令令史監、不從令者貲一甲」(1265)。
可知,无论是战国时期的秦还是在其统一中国之后,官吏在进行商业活动的时候,都由令史在现场对其进行监管。因此,史料A中的“令市者見其入”难道不正是指这件事吗。所以在这里应该解读为“市者=令史”。根据以上的考证,史料A的意思大致应如下:
从事手工业者和官府中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如果领受了钱的话,必须立刻将其放入“缿”内,并且其装钱的过程也需在市者(令史)面前进行。若有人不从令的话则貲一甲。关市。
那么,对于被装入“缿”之后的钱又该如何进行处理呢。显示此内容的史料如下:
D.官府受錢者、千錢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錢善·不善、雜實之。出錢、獻封丞·令、乃發用之。百姓市用錢、美・惡雜之、勿敢異。金布(金布律131-132)。
由此可知,似乎将钱以每一千枚为一个单位划分出来,并由“丞·令印”对其进行封缄,然后妥善保管。因此,可以将前面引用的秦律的内容大致复原为图2。
2.西汉初期在“市”进行的“受銭”
那么,上述官吏在“市”进行“受銭”的状况在之后是如何被继承的。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记载。
E.官爲作務市及受租質錢皆爲缿封以令丞印而入與參辧券之輒入錢缿中上中辧其廷質者勿與券租質戸賦園池入錢縣道官勿敢擅用三月壹上見金錢數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上丞相御史(金布律429~430)。
首先需要对本条的成立年代进行确认,文中出现有“丞相·御史”,这应该就是“丞相·御史大夫”的略称[11],那么这些中央官职是于何时设置的呢,根据流传下来的文献,关于西汉初期“丞相”的设置时期见图3,可得知有两个时期,一个是中央置相国而在诸侯国置丞相的时期(前194~前189),另一个是中央置丞相而诸侯国置相国的时期(前202~前196)。因此含有作为中央官职的“丞相”的这一条应是在汉十一年(前196)以前或惠帝六年(前189)以后规定的。众所周知,《二年律令》因含有吕后二年律,所以惠帝六年之后的可能性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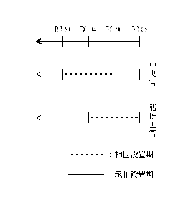
〔圖3〕丞相和相国的設置
接下来需要对其内容进行确认,和秦律相同,首先对在开头出现的“官爲作務市”的解读方法中存在问题。目前有两种可能性。①在市进行作务的官方人员
②进行作务和商务活动的官方人员
然而,前面出现的秦律中,和这一条相近,“作務”和“官府市”相并列,并用“及”字断句。而本条则和其相似,“爲作務”和“市”亦为并列关系,如果按照②的读法,本条可以翻译如下:
官方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人员及收取市租和质钱的官方人员均须制作“缿”(装钱的容器),然后以令·长·丞的印将其封缄。并给予支付钱者参辦券,此时,将钱装入“缿”内,并将(参辦券里的)中辦向(县或者道)的“廷”缴纳。另外参辦券中的其中一份不发给质者。装入市租·质·户赋·园池(作为收入)的钱,县官和道官不得擅自使用。(县官和道官)每三个月将其所保管的黄金及钱数呈报至两千石的官员,然后再由两千石的官员转呈给丞相及御史大夫。
通过这项规定,可知券书(即參辧券)所起的作用极为重要,“參辧券”的“辧”意为分发,“券”是证书,因此,“參辧券”应是一种割符。而对于“參”字则有两种说法。
①将割符分为三份。即“參辧券”是一种可以分为三份的割符[12]。
②“參”的意思和“雜”字相同,即管辖范围不同的官员们共同处理事务。那么,“參辧券”就是在官员们都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分发的券[13]。
在这一条后面部分有“中辧”,应是“參辧券”其中的一份,那么本条中的“參辧券”似乎可以被分作上·中·下三份。也就是说,持钱者、保管“缿”者以及(县、道)的“廷”三者似乎应该分别持有一份券。
因此本条中的纳税程序如下:首先,持钱者将带来的钱缴纳至负责此事官员的“缿”里,此时他会得到一份作为领受钱的证明,即一份参辦券。另外,由于装有钱的“缿”被令、长、丞的印封缄了,所以对其负责的官员无法直接接触到钱。之后被缴纳的钱通过负责此事的官员被提交至县及道的“廷”,随后才被令、长及丞首次开封。而且,为了证明“缿”里的钱被准确无误的递交到了“廷”,负责的官员必须再向“廷”提交一份参辦券。因此可以得知,汉代初期实际的纳税情况是:通过持钱者、有关的负责官员以及(县、道)的“廷”三者均持有的一份参辦券,起到证明钱的缴纳和受领的作用(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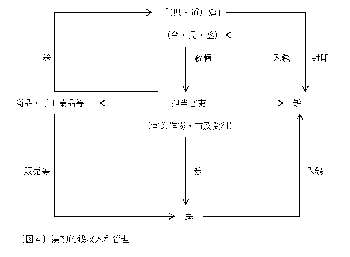
3、西汉时期的“质钱”(抵押金)的禁止
关于“质者勿予券”,京都大班等,将其译为“作为抵押的人,不能发给他券”[14]。但是,这句话的前后文均与钱有关,所以,很难把这里的“质者”考虑为所指的是用人来抵押。倒不如说本句的意思可能是,付了“质钱”借了官方所有器物等的人,不发给他们“參辧券”中的一部分。据此,可认为缴纳“质钱”的时候,仅是由负责将“质钱”保管在“缿”里的官吏和“廷”(县或道的),这两者来分配并持有“參辧券”。那么,到底为什么不能发给上述这些与“质钱”有关的百姓“參辧券”呢?
本来百姓在缴纳“质钱”的时候,不发给其“參辧券”,就意味着那个人自己不能证明缴纳了“质钱”这样一个事实。这样的话,借了官方所有器物的百姓在返还的时侯,如果负责管理“缿”的官吏造假说,“并无保管质钱的纪录”,那么未持有“參辧券”的百姓则无法反驳。这里要注意的是,秦律和汉律里都有禁止官方强制地收取“质钱”的条例。
F.諸有責(債)而敢強質者、罰金四兩(《二年律令》襍律187)。
G.百姓有責(債)、勿敢擅強質。擅強質及和受質者、皆貲二甲。廷行事強質人者論、鼠(予)者不論。和受質者・鼠(予)者□(不)論(《法律答問》518)。
据此,百姓在要求退还“质钱”时,负责的官吏若是不应许,就成了从百姓那里强行地攫取“质钱”,这样就触犯了上述襍律。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负责的官吏窜改了“參辧券”的内容,百姓的诉讼也会被驳回。或者,百姓在返还所借官方所有器物时,将缴纳的“质钱”的面额多谎报的可能性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总而言之,史料E,F未必成为不发给“质者”字据的积极的理由。
这里值得注目的一点是,史料F的“质钱”并非是官方强制征收的,而是官方和百姓之间“和”(达成协议)的结果,是官方从百姓接收的东西,且在此过程中一次字据的交换也没有产生。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持有字据的仅仅是官方(负责的官吏及县或道的“廷”)。总之,这个字据,最终仅仅是为了证明负责的官吏在给“廷“提交“质钱”时,并未伪造的证据而已,并不是为了证明百姓和官方之间收受“质钱”这一事实。这就意味着关于“质钱”的收受,官方与百姓之间的“和”“(达成的协议)并不是建立在字据上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百姓在借官方所有器物时,一旦缴纳了“质钱”,之后即使是拖欠?不履行债务?,还是有着将“质钱”拿回的潜在权利。这一推断成立的话,百姓所缴纳的“质钱”只是一种形式,官方也只是对“质钱”进行一时的保管而已。那么,为什么官方要将“质钱”进行一时的保管呢?
这里要注目的史实是,在战国的秦,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官民之间收受“质钱”都是被禁止的。即是说在战国的秦时,在“和”的基础上,有官方从百姓那里收取质的案例,但是作为其法律依据的秦律,却是禁止了官强制民交纳“质”,以及在“和”的基础上,收取“质”这两种情况的。这就意味着,《二年律令》的“质钱”是继承了战国的秦时的“廷行事”(廷的案例)的。也就是说,战国的秦在当初虽然禁止了一切的“质”的收受,但是之后,据民间的具体实情案例又允许了其中一部分的存在。而这可以认为是被汉律所继承了的。若是那样,是否可以认为在汉初,官方是不应收取“质”这样一种思想是依然存在的。这样考虑的话,本条中,官方不接受“质钱”,而仅仅是暂时保管的理由也就清楚了。换言之,因为官方本来是不应该从百姓那里收取“质钱”的,所以不是采取受领,而是采取在原则上仅为保管的这样一个立场。正因为如此,在本条中规定了对专诚带来“质钱”的百姓,也不要发行字据,以免将缴纳“质钱”义务化了。
这样一种“官吏本来不应该从百姓那里收受“质”的思想,在这以后也被继承着。比如说,据居延肩水金关出土的汉简(74:E.J.F16:1-16。即所谓的《永始三年诏书》[15]),在永始3年(前14)以前的“三辅”地区,“豪黠官吏”(蛮横狡猾的官吏)借给百姓物品,并以此收取“重质”的情况曾很普遍,由于这是欺压百姓之举,所以应被禁止的这样一个宗旨是被(皇帝)敕许了的。那么,到底为什么官吏从百姓那里收取“质钱”被认为是不应该呢?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质”的渊源,被认为原本是指,春秋时期以前各国间外交时所交换的人质。这样的取“质”(抵押人质)的外交惯例在战国时期以后,逐渐受到了批判[16]。小仓芳彦作为其例,把《春秋左氏传》隐公3年列举了出来。
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
而且将这种想法认为是“儒家思想对于法家思想对的否定和排斥”。
另外,关于官吏和〈质者〉(拿“质钱”来作抵押的人)之间不交换字据,在《史记》卷75孟尝君列传中也可看到如下的类似的例子。也就是,在战国的齐,“薛”的邑主孟尝君本来借给了百姓很多钱,百姓当中不偿还借款的也有很多,渐渐地孟尝君自己的财政也陷入了困境。于是孟尝君命令部下冯驩,想从百姓那里收回借款。但是冯驩却把欠钱的百姓聚集起来,当着百姓的面把证明孟尝君借给百姓钱的“字据”的大部分都烧了。为此孟尝君勃然大怒,而冯驩却做了以下的说明。
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虚債之劵、捐不可得之虚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史记》卷75孟尝君列传)。
据此可以认为与“质者”之间不交换字据,在当时是被认为和“亲君”(使民心向着君主)相关联的。如此,《二年律令》中的“官吏不应该收受“质钱”,即使接受了也不应该发行字据”这样一种想法,其存在的背景可以认为是受了像这样的重视“礼”,“亲”的当时的思想的影响。
若上述推测无大纰漏的话,可以说西汉帝国未必只是重视了确保利益(财政收入)。西汉帝国在“受钱”(收取货币形式的税金以及由交易而得的货币收入等)时,为避免发生不周而格外小心谨慎的同时,相反地,也保持了重视“礼”,“亲”的姿态。
结语
本报告就以下两点进行了论述。
1 战国的秦到西汉初期的纳税手续,可如图2,4一样复原。据此,可知当时的国家实施了严格的纳税制度,而且到西汉初期变得更为严密。
2 但在西汉初期,也存在着“官吏不应该收受“质钱”,即使接收了也不应该发行字据这样一种思想。因此相反的可以看出,比起财政收入来,国家更重视百姓的姿态。
总而言之,西汉帝国在实施严格的纳税制度的同时,也“导演”着如2所示的宽大,将露骨的国家权力掩盖起来,以图其安定的统治。
(編者按:本文收稿日期為2009年6月25日。)
[1]在此,将笔者发表过的有关中国古代货币经济的拙稿例举如下。
①「殷代宝貝の社会的機能について――中国貨幣史の始源を探るための基礎的検討――」(『歴史民俗』第2号、2004年)
②「秦漢時代における物価制度と貨幣経済の構造」(『史観』第155冊、2006年)
③「漢代における銭と黄金の機能的差異」(『中国出土資料研究』第11号、2007年)
④「文字よりみた中国古代における〝貨幣〟の展開」(『史滴』第29号、2007年)
⑤「秦漢帝国による「半兩」銭の管理」(『歴史学研究』第840号、2008年)
⑥「前漢初期における盗鋳銭と盗鋳組織」(『東洋学報』第90巻第1号、2008年)
⑦「戦国秦漢時代における布帛の流通と生産」(『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第9号、2008年)
⑧「戦国秦漢貨幣経済の特質とその時代的変化」(成均館大学校BK21事業財団主催国際学術大会「東アジア歴史学新進研究者国際学術大会(予稿集)」、2009年1月17日、於大韓民国成均館大学校)
⑩「殷周時代における宝貝文化とその「記憶」」(工藤元男・李成市編『東アジア古代出土文字資料の研究』雄山閣、2009年)
⑪「中国古代貨幣経済史研究の諸潮流とその展開過程」(『中国史学』第19号、2009年刊行予定)。
[2]重近啓樹「商人とその負担」(同『秦漢税役体系の研究』汲古書院、1999年)
[3]佐原康夫「漢代の市」(同『漢代都市機構の研究』汲古書院、2002年)
[4]陶安あんど「貲刑――非刑罰的制裁措置の編入」(同『秦漢刑罰体系の研究』創文社、2009年)
[5]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
[6]据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龍崗秦簡』(中華書局、2001年)。袁仲一・程学華「秦代中央官署製陶業的陶文」(『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佐原康夫「秦漢陶文考」(同『漢代都市機構の研究』汲古書院、二〇〇二年)这两篇论文考证,在战国秦的民间手工业者中也有官属的一部分人。
[7]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注5前掲書。
[8]Hulsewe A.F.P (1985) REMNANTS OF CH'IN LAW, LEIDEN: E.J. BRILL
[9]山田勝芳「その他の諸税」(同『秦漢財政収入の研究』汲古書院、一九九三年)、堀敏一「中国古代の「市」」(同『中国古代の家と集落』汲古書院、一九九六年)、佐原注3前掲論文、重近注2前掲論文等。
[10]陈长松「岳麓书院收藏的秦简综述」(『文物』2009年第3期)。
[11]关于『漢書』巻19百官公卿表上・御史大夫条的陳直『漢書新証』「御史大夫與丞相連稱者、簡稱爲丞相・御史。高祖紀所謂制詔丞相・御史、是也」。
[12]整理小組等。
[13]籾山明「刻歯簡牘初探――漢簡形態論のために――」(『木簡研究』第17号、1995年)。
[14]冨谷至編『江陵張家山247号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訳注編(朋友書店、2006年)。京都大以「入與參辨券」的「入」字为「人」。但是「二年律令」中的「入」字和「人」字的字形上的区别很难。特别需注意的是关于本条的「入」字和後掲金布律(433)的「入」字的在字形上极为相似。
[15]甘肅省博物館漢簡整理組「《永始三年詔書》簡冊釈文」(『西北師院学報』1983年第4期)、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新簡釈粹』(蘭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关于这个本册书内容,大庭脩「肩水金関出土の「永始三年詔書」冊」(同『漢簡研究』同朋舎、1992年),山田勝芳「その他の諸税」(同『秦漢財政収入の研究』汲古書院、1993年)也参照。
[16]小倉芳彦「中国古代の「質」――その機能の変化を中心として――」(同『小倉芳彦著作選Ⅲ 春秋左氏伝研究』論創社、2003年)。
© Copyright 2005-2021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