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所見刑手、刑足、斷足、踵(腫)足、雀(截)手、雀(截)足的思考
作者:郭聰敏 發布時間:2014-03-23 09:51:23
(鄭州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自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出土以後,學者們從不同的學術角度對簡文中刑(
關鍵字:吳簡 刑手 刑足 斷足 踵足 截手 截足 肉刑
前 言
徐世虹先生發表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所見刑事制裁記錄》一文首次將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後文皆簡稱作吳簡)中“刑(
有學者們以醫學或從長沙地區的氣候等視角分析,將吳簡所見“踵(腫)足”解釋為血絲蟲病或凍傷的結果。[6]
有學者們解釋“雀(截)足”為一種傷殘。[7]
本文從法律史的角度觀察認為,吳簡所見刑(
正 文
一、字形演變
市面上學者們對吳簡中的“刑(
“刑”字的演變。依史料認為,“井”為“刑”字的最早寫法。“井”字的本義是水井,如《世本》中有“化益作井”[9]的說法。之後“井”引申為刑法或法律的意思,如《越絕外傳記地傳》“……祀白馬禹井。井者,法也……”[10]中的“禹井”即是《左傳》“夏有亂政,而作禹刑”[11]中的“禹刑”。《風俗通》也有解釋:“井者,法也,節也,言法制居人,令節其飲食,無窮竭也。”[12]也就是說,早期只有刑法或法律意義上的“井”才能做“刑”的通假字。


西周晚期金文中出現了“
陳夢家在《西周銅器斷代·免毀》中總結:西周金文隸定為井者,如取範型象形(鑄造青銅器所用模範的象形)井字:開類,兩橫平行,兩直畫常是不平行而是異向外斜下的,中間並無一點。[14]推測“井”字形在寫法上應類似“
秦時李斯奉命篆寫的《會稽刻石》中有“
隸書其實在秦統一之前就已在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流行起來,考古學家在秦國發現了隸書文字,足以證明其出現幾乎與篆書同時代。秦統一文字之後,與篆書相比,因為其符合文字由繁化簡的必然發展規律,因此篆書輕易地就為隸書所取代而被淘汰。兩漢時期挖掘出來的簡碑帛文字一般為隸書,如漢馬王堆帛書見隸書“
據史料講三國時期曹魏方著名書法家鐘繇始創楷書,但查鐘繇書法碑文尚未見“刑”字。查唐人顏真卿楷書“
據專家統計,吳簡中95%以上都寫作“刑”(如【左圖】所示),只有不到5%寫作“
二、定義與關係
第一階段我們已從字形上對“刑”字完成了確認,那麼吳簡中的“刑”到底是什麼意思?“刑手”、“刑足”究竟是傷是病還是刑罰呢?與之格式相似的大量“斷足”“踵(腫)足”、“雀(截)手”、“雀(截)足”簡是否與“刑手”、“刑足”簡存在著某種關聯呢?這些即是我們在第二個階段裏將要重點分析的問題。
(一)“刑”的定義
“刑”一般可以解釋為靜態的名詞(如刑法)或動態的動詞(如殺戮、刑罰),在吳簡的釋文語境中分析,如:9-2889 .義成里戶人公乘黃朔年63刑右足。[19]其中“刑右足”的“刑”首先應被理解為動詞,因此就排除了名詞性的刑法,只能保留殺戮、刑罰之意。《國語·卷四·魯語上》:“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紿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鋮,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簿刑用鞭撲,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20]此處,對外的軍事征伐之“刑”與對內的刑事制裁之“刑”混為一談。大刑包括甲兵、斧鋮,中刑包括刀鋸、鑽笮,簿刑包括鞭撲。那麼“刑手”、“刑足”是到底屬於哪一類等級的“刑”呢?我們認為吳簡中的“刑”應屬於“中刑”中的刀鋸之刑,因為《國語·魯語上》載:“中刑用刀鋸”。韋昭注:“割劓用刀,斷截用鋸”。[21]作為戶籍簡中的戶民,“刑”只可能是對內的刑事制裁,因此排除了大刑;那倘若是簿刑鞭撲的話,是不可能區分鞭撲左右手足的。固而可以斷定吳簡所見“刑”應為用鋸斷截肢體的刑罰。
(二)“刑”、“雀(截)”、“斷”的相互關係
“雀”字在字形及發音上與“截”字相似,因此可以理解成古人在戶籍登記時的一種疾筆快書,“雀”應是“截”的誤釋,後文方便起見論述時只用“截”字。推測“截”與“刑”同義,如下列吳簡兩次對範宜的右足狀況使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
1.9861 .民範宜年30雀右足/。[22]
2.1764 .民男子范宜年42刑右足。宜妻大女年32算一。[23]
另外“截”也與“斷”同義,如:
3.3369 . 騰兄公乘鬥年33算一雀兩足複。[24]
2.2939 .·騰兄公乘鬥年51算一斷足以嘉禾5年10月20日被病物故。[25]
至此,我們有了“截”與“刑”、“斷”同義的結論。
此外,推測“刑”與“斷”同義。《韓非子》曰:故仲尼說隕霜,而殷法刑棄灰。[26]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鬥,鬥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一曰:“殷之法,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27]依描述,“刑棄灰於街者”具體落實下去就是“斷其手”,即刑、斷、截可以互換。
(三)“刑”與“踵(腫)”的關係
據《莊子·德充符》記載:“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這裏的“踵”即是因為“無趾”,而用腳後跟走路的意思。“天刑之”的“刑”應是抽象意義上包含一切肉刑的刑罰,材料似乎可以證明“刑”包含“踵足”。“踵”與“腫(腫的繁體字)”在書法時幾分分辨不清,在吳簡的語境中,我認為如果將其理解為血絲蟲病或凍傷的“腫”可重可輕,沒有可依據的固定標準,是完全不符合戶籍登記原則的。吳簡只見有“踵左足”“踵右足”並不見“踵手”,如果是血絲蟲病或凍傷不可能只涉及腳部,也完全沒有必要對可輕可重的“腫足”作左右之分,因而認定吳簡所見為“踵”較之“腫”要更合理一些。
(四)“踵(腫)足”與“刖足”的關係
刖足其實包含著兩種刑罰方式,一種是自腳腕以下全部截斷,一種是斬斷腳趾。
雖然西漢時漢文帝廢除了肉刑,但據《後漢書卷六十下·蔡邕列傳第五十下》載:“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28]蔡邕生活在東漢靈帝時期直至董卓時期,請求赦免死刑改為刖足之刑保存生命,證實肉刑依舊在事實上存在,最起碼刖足之刑仍在使用,同時也似乎說明了刖足是低次於死刑的一種刑罰。
再根據《三國志·吳書·孫皓傳》云:“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流殺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裴松之注云:“吳平後,晉侍中庾峻問皓侍中李仁曰:‘聞吳主剝人面,刖人足,有諸乎?’仁曰:‘此告者過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為酷虐。皓為一國之主,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又問曰:‘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對曰:‘視人君相迕,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29]李仁為孫皓實施剝人面、刖人足、鑿人之眼進行辯護,這說明孫吳方確實使用過剝人之面、刖人之足和鑿人之眼的肉刑。
此外《晉書·刑法志》西晉初期司法官劉頌曰:亡者刖足,無所用複亡。盜者截手,無所用複盜。……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恤養,不流離于途路。[30]引文可知,其中的“刖”也可與“刑”互替。
綜合前述的比較,吳簡中的“刑足”與“踵足”應皆統稱古代刑法概念上的“刖足”,大概“刖足”是作為法律上的專門刑名,由於戶籍登錄服務于統治者的利益,故而會用一些描述性的詞語對刑罰後的情況進行簡要地區別或說明,因而“刑”“踵”這樣生動的詞語便被用以修飾罪犯的現狀。繼而推測“踵足”只是砍掉腳趾,尚能走路;而“刑、截足”應是自人的腳腕以下全部砍掉,已無法走路。
那麼我們可以就此認定,吳簡所見刑手、刑足、踵足、截手、截足皆是刑罰也就是肉刑後的結果。有心者不難發現,吳簡中有刑手、刑足分為刑左手、刑右手、刑兩手、刑手、刑左足、刑右足、刑兩足、刑足,另有一些其他部位的刑罰(由於無關本文的觀點,故而不再分析),如刑兩膝、刑歐背、刑右眉、刑目、刑慮頭;截手、截足分為截左手、截右手、截兩手、截手、截左足、截右足、截兩足、截腳;一例斷足;踵足分為踵左足、踵右足、踵兩足、踵足。我們從現有史料中並沒有發現三國時期肉刑恢復的相關法條,但即便是法外用刑,如此細緻的分類,我認為應是肉刑的不同等級,即不同的犯罪後果適用不同輕重的肉刑,《莊子·養生主》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郭象為《莊子》作注云:“介,偏刖之名。”[31]刖去一隻腳者稱為偏刖,或者叫做“介”。至於犯什麼罪需要刖左腳,什麼罪需要刖右腳,可能也有一定的規定。《管子·地數》記管仲對齊桓公說:“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32]一般說來,視所犯罪行的輕重,較輕的罪行只刖一隻腳,特別重的罪才刖去雙腳。又如漢文帝廢肉刑,規定:“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皆棄市。”[33]可見斬右趾的刑罰比斬左趾重得多,也就是說右肢體要比左肢體重要。根據身體功能的重要程度,我大致對肉刑的種類作了這樣一個輕重排序:刑(或截)兩足、刑(或截)兩手、刑(或截)右足、刑(或截)左足、刑(或截)右手、刑(或截)左手;踵兩足、踵右足、踵左足。
第二階級中我們解決了這樣一些問題:吳簡中的“刑”是與“截”“斷”有相似的意思,雖然我們沒有確實見到東吳關於肉刑處罰的具體法條,但“刑手”、“刑足”、“踵足”在吳簡中被證實是一種肉刑,且二者在法律的專門術語是“刖足”。與之格式相似的大量“斷足”、“雀(截)足”簡是“刑足”簡的不同寫法,但意思相同,都是砍掉罪犯的腳;“雀(截)手”是砍掉罪犯的手。“踵(腫)足”是砍掉罪犯的腳趾。並且我有一個大膽的推論,雖然東漢、曹魏、西晉的史料並沒有恢復肉刑的記載,但東吳在政治動盪的非常時期,雖然也繼續延承了兩漢時期及效法了曹魏的法律制度,但我們不能因此否認特殊的個案出現,加之上述如此細緻地對左右手足進行不同輕重地歸類,東吳根據國情恢復肉刑並將其上升為法律制度是極有可能的。
三、罪名
那究竟是觸犯了什麼罪名才會處以這些層次分明的刑罰呢?
《晉書·刑法志》記載司法官劉頌曰:亡者刖足,無所用複亡。盜者截手,無所用複盜。[34]此處我們可以看到,西晉距三國時間很近,劉頌建議叛逃者處以刖足、盜竊者處以截手,我認為作為司法官這個建議不太可能是空穴來風,想必是前有刖足、截手的刑罰實踐,很有可能是希望將此司法實踐昇華到法律的條文之中。吳簡所見多處“叛走”簡,而劉頌“無所用複亡”所建議的方法即是“亡者刖足”,吳簡中有幾處官吏叛走簡,且標明了詳細的姓名、年齡與叛走時間,如下:
1.7868.縣吏毛車世父青年49,以嘉禾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叛走。
1.7882.郡故吏史僦北政年15,嘉禾四年四月十日叛走。
1.7903.軍故吏烝□兄
由於簡文大都出自嘉禾年間,我們來瞭解一下距離嘉禾年前後不遠的一些軍事事件。
黃龍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眾五萬討武陵蠻夷。
夏,中郞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淩,淩以軍迎布。
冬十月,權以大兵潛伏於阜陵俟之,淩覺而走。
嘉禾元年春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
秋九月,魏將田豫要擊,斬賀于成山。
冬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閬中令孫綜稱藩于權,並獻貂馬。權在悅,加淵爵位。
三月,遣舒、綜還,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舉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淵果斬彌等,送其首于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欲自征淵,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是歲,權討山越。
九月朔,隕霜傷穀。
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向合肥新城,遣將軍全琮征六安,皆不克還。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寬諸逋,勿複督課。”
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率大眾圍合肥新城。
未至壽春,權退還,孫韶亦罷。
秋八月,以諸葛恪為丹楊太守,事皆,還武昌。
詔複曲阿為雲陽,丹徒為武進。
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為亂。
四年夏,遣呂岱討桓等。
秋七月,有雹。
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玳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
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
二月,中郞將吾粲獲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
自十月不雨,至於夏。
冬十月,彗星見於東方。鄱陽賊彭旦等為亂。
二月,陸遜討彭旦,其年,皆破之。
冬十月,遣衛將軍全琮襲六安,不克。
諸葛恪平山越事畢,北屯廬江。[36]
史料所列,孫吳方面在此期間大規模地曾對武陵蠻夷、曹魏、山越、廬陵賊、鄱陽賊進行過征伐,加之三次天災以及對魏的“以物換馬”的軍事交易,就迫切需要源源不斷的大量軍資與兵員,那麼賦稅、徵兵就成為孫吳的政治當務之急,三年春正月的詔“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寬諸逋,勿複督課”[37]也擺明瞭百姓的負擔很重,而勞動力、兵力對於戰爭的供不應求使得主權者不得不加大對民眾的徭役力度及對官吏行政的督促力度,因此吏民“叛走”在所難免。在保留勞動力與制裁震懾的左右權衡中,肉刑“無所用複亡”的特點就成為孫吳統治者最省心的政治輔助手段。故而,吳簡中“刑足”“踵足”極有可能是犯了叛逃罪。
“刑足”也有可能是犯了不孝罪。秦《封診式》中有個案例:士伍咸陽某里人丙不孝,因其父甲請求將他斷足,流放到蜀郡,叫他終生不得離流放地點而定罪。由秦律可見,不孝罪有可能要被處以斷足之刑。三國時期對於不孝罪較之秦朝刑罰更重,有增無減,如《三國志·吳書》記載: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絰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是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群僚,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為節度。”顧譚議,以為“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列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為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為“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幹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至。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為臣,焉得兼之?故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其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于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因為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為此,因此遂絕。[38]從此資料來看,不孝罪原本在東吳是要被處以死刑的,雖然孫權“因為之請”,“乃減宗一等”,並規定“後不得以為此”,因此才“遂絕”,但我們可以在從史料中經常看到孫權的大赦或曲赦,只舉嘉禾年間的兩次大赦,如下:
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
二年春正月,詔曰:“……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39]
儘管孫吳方面觸犯不孝罪在法律上要被處以死刑,但如果趕上孫權大赦,則減罪一等,肉刑作為低死刑一級的一種有效刑罰,自然有其存在的可能。因此,東吳的不孝罪在死刑減刑或大赦後極有可能“刑足”或“踵足”。而如果一個刑名在法律上有所規定,按照常規理解,其刑種也是應當被記錄在法律之中的,因此,我仍然認為東吳在法律上已恢復了肉刑,而不僅僅只是單純的法外用刑。
由於“叛走”牽涉到戶籍的變動,屬於政治性犯罪,故而吳簡中會有專門的“叛走簡”,而“盜竊”只會引起財產的減少,故而戶籍簡中不必標明何人盜竊。“盜者截手”是指盜竊的人要被截手,結合“殷之法,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與“搏必隨手刑”[40],“刑手”極有可能是犯了盜竊、棄灰於公道、搏鬥這些跟“手”有關的罪,當然,秦《封診式·群盜》記載了一個案例,其中對於群盜罪犯是適用斬左趾為城旦,如有加罪情節,則斬左趾以黥為城旦,固而根據不同的惡性,肉刑部位是有所區別的。
至此第三個階段,我們基本上確定了一個主要問題,吳簡所見刑手、刑足、踵足是東吳根據不同的犯罪動機和犯罪行為處以相應部位的肉刑,而在刑罰時可能又根據犯罪的主觀惡性及危害後果處以輕重不等的肉刑,吳簡所見“刑足”、“踵足”可能是觸犯了叛逃罪、不孝罪,所見“截手”可能是觸犯了盜竊罪。當然,我們只能簡單地根據已有史料大致地對一些罪行配以基本相應的罪名及刑種,事實上適用一個刑種會是因為觸犯了多種多樣的罪名,因此我並不敢將這些史料作蓋棺定論,只是在現有簡文中抽取幾個典型罪名、刑種作以僅有的揣測。
此外,從簡3.3003.戶人見一人任吏□□刑腫叛走以下戶民自代□□□□人名年紀為簿[41]中大約可以推測出吳簡所見“刑手”、“刑足”、“踵足”刑事犯罪者很有可能是與普通居民戶籍簡區別出來單獨羅列成籍的。
四、犯罪主體
讀者不禁要問,為什麼吳簡“刑、踵者”上至97歲老者(2.2980 .大成里戶人公乘烝狶年97刑左手腫兩足[42])下至4歲幼童(3.947 .想男弟禿年4歲刑右足[43])都未能免遭重刑?我認為吳簡中叛走者大多不是單個人逃亡,很可能是一種集體行為以及連坐的結果。
赤壁之戰以前,自孫吳集團拒隅江東,與北部曹、劉集團極少正面大規模地發生衝突,注意力集中在招降邊疆的武陵、山越等少數民族上,如下圖所圈劃範圍,武陵蠻夷可以很輕易地叛逃到蜀國,山越在東北部更是可以輕易地叛逃至魏國,尤其是孫權在山越人的問題上征戰持續了多年,史料講孫權也在招順之後還新置了東陽縣等一些新縣向內遷徙以供山越人居住,並對願意遷入新置縣的山越人賜“公乘”這樣的民爵。但這些居民區緊依東吳邊疆,仍舊遠離政治腹地,不容易被中央所控制。佔用土地的最好辦法即是居住百姓,而邊境地區又是國外勢力經常侵犯的必經之地,一旦有敗,百姓極易叛逃或投降他國。除前述所列官吏叛走簡,吳簡(三)還出現了一些普通民戶叛走簡,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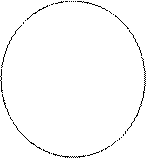

3.231 .蜀弟蕙年42隨蜀俱叛
3.1788.倉女聟楊□年18以嘉禾4年3月18日叛走
3.2981.□子男丹年16一名耳 俱叛
3.2981.□男弟囊年17隨□在□俱叛 中
3.6104.叛弟小男建年7歲
3.1584.□侄子集年11 與記俱時叛走[44]
沈剛先生在《“叛走”簡剩義》中認為這幾隻簡是吏的家屬與吏一起叛走。[45]下面一條更可以坐實沈剛先生的判斷:
3.3270.右民六戶□(可能缺“叛”字)走入泠道湘西醴陵/。[46]
“民六戶”顯示“叛走”的主體應是集體,吳簡所標示出來每一戶的家庭關係有夫妻、父子、父女、母子、兄弟、叔侄等,這就大致解釋了吳簡中出現的婦女、兒童被肉刑的現象。如下:
1.8638 .知男弟堂年5歲刑左手。堂男弟春年5歲刑左手。[47]
2.1587 .倫兄公乘觀年41刑右足。觀妻大婢年45刑□□。
2.3100 ./。妻大女姑年65刑左足。小妻大女思年44算一腫兩□。[48]
此外有公乘身份的人如果受“刑”、“踵”,通常都是單獨成一簡,如下:
1.8692 .東陽里男子戶人公乘□□年22算一刑左手。
1.7420 .東陽里戶人公乘鄭□年47算一刑右手。
1.10462.東陽里戶人公乘朱就年66刑右手。
1.9252 .東陽里戶人公乘文兩年81腫兩足。
2.2903 .高平里戶人公乘黃高年52算一腫兩足。
1.3071 .常遷里戶人公乘鄧卿年33算一刑左手複。
2.3313 .大成里戶人公乘梅敬年44刑左手/。
9-2889 .義成里戶人公乘黃朔年63刑右足。
3.6163 .義成里戶人公乘杜從年36踵兩足。
1.8515 .義成里戶人公乘壬盡年58腫兩足。
1.10385.吉陽里戶人公乘勇客年41算一腫兩足。
1.9508 .曼浭里戶人公乘逢揖年39算一刑左手。
1.951 .祐樂里戶人公乘□□年17刑右足。
1.10289.高遷里戶人公乘張像年40算一刑右足。
1.10321.高遷里戶人公乘唐星年76腫兩足。
2.4502 .安陽里戶人公乘□表年45算一腫兩足·。
1.9212 .石門里戶人公乘廬仵年48雀左手一點一橫+目。
1.9162 .石中里戶人公乘□草年45算一刑右足。
2.2984 .平陽里戶人公乘張物年60刑右足。
1.10475.平陽里戶人公乘劉戰年58刑兩足。
3.6227 .富貴里戶人公乘革□年50踵右足。妻汝41算一。注:41上脫年字。
1.8436 .東夫+夫里戶人公乘陳每年42算一刑右足。
1.8441 .東夫+夫里戶人公乘仇莫年69腫兩足。
1.9234 .東夫+夫里戶人公乘□謙52算一腫兩足/。注:52上脫水年字。
1.9388 .□□里戶人公乘□□年26刑左足。
3.3131 .□□里戶人公乘廖古年48刑兩足/。
2.4507 .□□里戶人公乘黃蕙年35算一腫兩足。訾50。
1.5456 ./ 里戶人公乘秦頡年23□右足。
2.4361 .□□里戶人公乘年□□腫足。/。
1.7325 .小赤里戶人公乘杜東年42算一腫兩足。
3.5644 .…… 戶人公乘逢樵年63雀左足。[49]
我們完全作可以這樣推測:公乘一般是戶人,即一家之長。具有公乘身份的人雖然只是民爵,但一般擔任著基層職務,如《居延漢簡》中記載:
肩水候官並山隧長公乘司馬成,中勞二歲八月十四日。
/和候長公乘蓬士長富,中勞三歲六月五日。[50]
吏其實是一種高級服役,當其刑事犯罪時,以其家長及其擁有爵位者或官位的高身份為軸心向其整個家庭四面輻射,因此即發生了家庭成員連坐受刑的現象。
三國時期實行連坐制度。如:
《三國志·魏志·高柔傳》載:“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51]
《三國志·魏志·毌丘儉傳》載毌丘儉、文欽上表曰:“又故光祿大夫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並及母后。”[52]
《三國志·魏志·三少帝紀》:“又尚書王經,凶逆無狀,其收經及家屬皆詣廷尉。”[53]同書《魏書·諸夏侯曹傳第九》注引《世語》曰:“經刑於東市,雄哭之,感動一市。刑及經母,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54]
可見,三國時期曹魏方面夷族妻子、子女及母親同居者都要連坐。吳簡中雖未直接寫明家庭連坐,但由“官連坐”的簡文大約也可以推測出家庭連坐也是存在的。如:
東鄉勸農掾殷連被書條列州吏父兄人名年紀為簿。輒科核鄉界,州吏三人,父兄二人,刑踵
廣成鄉勸農掾區光言:被書條列州吏父兄子弟伏處、人名、年紀為薄。輒隱核鄉界,州吏七人,父兄子弟合廿三人,其四人刑、踵、聾、歐病;一人被病物故;四人其已送及,隨本主在宮;十二人細小;一人限佃;一人先出給縣吏,隱核人名、年紀相應,無有遺脫。若後為他官所覺,光自坐。嘉禾四年八月廿六日破□保據。(無編號)[55]
“若為他官所覺,連自坐”、“若後為他官所覺,光自坐”講的是“官吏職務連坐”。
“州吏三人,父兄二人”、“州吏七人,父兄子弟合廿三人”若非集體叛走,就是家庭叛走連坐。
《漢書·刑法志》載:“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太尉、禦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評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56]連坐的目的是“累其心”。那麼如果孫吳集體實行肉刑連坐,一方面是想保留勞動力,另一方面又想讓吏民放棄或打破犯罪的計畫或再犯罪的計畫。但無論是集體叛走或是職務連坐又或是家庭連坐,我們現在都可以認定其為共同犯罪行為。
據此,我們又可以推測出吳簡所見肉刑應有單獨犯罪、共同犯罪,對於隱瞞、包庇的官員實行職務連坐,對於集體犯罪行為可能實行集體肉刑連坐,對於罪犯的其他家庭成員可能實行家庭連坐。
五、肉刑恢復的背景
解決了以上問題,緊接著就有人會問:漢文帝時就已廢除了肉刑,為什麼到三國東吳這裏又恢復了呢?我的意見是孫吳集團在治國方面遵循了兩條線,一條是仍延續兩漢的儒家政治理念,一條是軍政治國策略,細緻起來恢復肉刑大致有三種需要:
第一,法律上的需要。肉刑是次於死刑一級的一種刑事手段,填補了死刑與徒刑之間的空檔。《三國志》孫權大赦或曲赦死刑,但只是赦免死刑,並不等於免除了其他刑罰,我認為部分肉刑者是由於單獨觸犯了某種相配套的刑罰,部分肉刑者極有可能是減刑之後的結果。
第二,補充了軍需。以戰俘或罪犯充當官奴同時在生理和心理上兩方面對其進行奴役。如秦代斬左趾主要作為城旦的附加刑而合併使用,肉刑後收為官奴繼續服役。
第三,政治穩定的需要。肉刑更可以起到殺一儆百、以儆效尤的效果,在少數民族大量聚居的東吳地區實行肉形,顯然可以對土著人起到一定的震懾作用。
總 結
本文解決了這樣幾個問題:孫權時期東吳區域以軍政治國,偏重重刑主義,恢復了肉刑,吳簡所見刑(
(附記:此拙文為2013年11月中國政法大學第四屆張晉藩法律史基金會優秀論文,《新路集第四集》待刊,預計2015年刊發,考慮到新出土簡版研究的時效性,故而將此文公開于此,敬請學界專家不吝斧正。拙文系筆者第一篇吳簡論文,寫作過程中承蒙姜建設、宋四輩先生支持,在此一並感謝。)
(編者按:本文收稿日期爲2014年3月22日14:20。)
[1]參見徐世虹:《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所見刑事制裁記錄》,《簡帛研究2001》下冊,第523——529頁。
[2]于振波認為:刖刑已被鈦刑代替,曹操、曹丕和曹叡統治時期,鐘繇先後三次主張恢復肉刑,都因其他大臣民的反對而未果。參見于振波:《走馬樓三國吳簡“刑手”“刑足”考——兼論歷史上禁止自殘的法律》,《簡帛研究》2003年10月11日,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簡帛研究網站。
曹旅寧認為:根據《史記·文帝紀》及《漢書·刑法志》記載,漢文帝十三年刑制改革廢除肉刑,刖刑、斬趾刑自此不復行用。雖然東漢、曹魏、兩晉時期有關“肉刑”的興廢討論屢見於史籍,但除了腐刑、黥刑尚有記載外,其他肉刑始終未付諸實施。參見曹旅寧:《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刑手”“刑足”考釋》,廣東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
王素認為:漢代已廢肉刑,直至曹操當政時期也未恢復,反駁徐世虹肉刑說。參見王素:《關於長沙吳簡“刑”字解讀的意見——<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釋文探討之一》,《簡帛研究2006》,第274頁——第281頁。
[3]于振波認為:吳國由於賦稅徭役沉重,百姓流亡、棄嬰乃至叛逃事件時有發生,考慮到三國之前和三國之後各個時代都有由於苛政導致百姓自殘的史實,吳簡中的刑手、刑足是苛政所造成的惡果,是貧苦百姓為逃避苛政的自殘行為。參見于振波:《走馬樓三國吳簡“刑手”“刑足”考——兼論歷史上禁止自殘的法律》,《簡帛研究》2003年10月11日,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簡帛研究網站。
[4]謝桂華只一筆帶過地寫到“刑”是殘疾病症,之後再無作其他解釋。參見謝桂華:《中國出土魏晉以後漢文簡紙文書概述》,《簡帛研究2001》下冊2001年9月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第546頁——第559頁,其中第556、557頁。
[5]參見胡平生:《從走馬樓簡“
曹旅寧認為:吳簡中有五例刑手、刑足者的年齡都是未成年或極其年幼者,顯然有可能是先天殘疾。部分認同胡平生先生的作戰殘致說。參見曹旅寧:《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刑手”“刑足”考釋》,廣東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
[6]參見汪小恒:《吳簡所見“腫足”解》,《歷史研究》2001年第四期,第174——175頁。
參見曲柄睿:《腫足新解——長沙走馬樓吳簡所見的一種病症考述》,《吳簡研究》第3輯。
[7]參見福原啟郎:《長沙吳簡に見える“刑” に関する初步的考察》,《長沙吳簡研究報告》2004年7月第2 集,日本·東京·長沙吳簡研究會,第69——84頁。
[8]參見胡平生:《從走馬樓簡“
[9]《二十五別史·世本作篇·堯》。
[10](東漢)袁康:《越絕書·越絕卷第八·越絕外傳記地傳第十》。
[11](春秋)左丘明:《左傳·昭公六年·傅》。
[12](漢)應劭:《風俗通義校注·佚文·市井》。
[13]西周厲王時期《散氏盤銘文》,又名《矢人盤》,現《散氏盤》存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14]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六)·87.免毀》,考古學報2004年4月版,中華書局,第107頁。
[15]前引注釋4《中國出土魏晉以後漢文簡紙文書概述》。
[16](漢)許慎:《說文解字》。
[17]同上書。
[18]王素:《關於長沙吳簡“刑”字解讀的意見——<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釋文探討之一》,《簡帛研究2006》,第274頁。
[19]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上)》,文物出版社,第32頁。
[20]《國語·卷第四·魯語上》。
[21]同上書.
[22]長沙簡版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下》,文物出版社。
[23]長沙簡版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貳)下》,文物出版社。
[24]長沙簡版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三)下》,文物出版社。
[25]同注釋23。
[26]《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經二必罰》。
[27]《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說二》。
[28]《後漢書卷六十下·蔡邕列傳第五十下》。
[29](晉)陳壽:《三國志·卷四十八吳書三·三嗣主·孫皓》。
[30](唐)房玄齡:《晉書·刑法志》志第二十。
[31]《莊子·養生主》。
[32]《管子全譯·管子輕重·地數第七十七》。
[33]《漢書·刑法志》。
[34](唐)房玄齡:《晉書·刑法志》志第二十。
[35]同注釋22。
[36]《三國志·吳書》。
[37]同上書。
[38]同上書。
[39]同上書。
[40](漢)司馬遷:《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41]同注釋24。
[42]同注釋23。
[43]同注釋22。
[44]同注釋23。
[45]參見沈剛:《“叛走”簡剩義》,《吳簡研究》第三輯,北京吳簡研討班編,崇文書局。
[46]同注釋22。
[47]同注釋22。
[48]同注釋23。
[49]同注釋22、23、24。
[50]《居延漢簡釋文合校》179.4.
[51](晉)陳壽:《三國志卷二十四·魏書二十四·韓崔高孫王傳第二十四》。
[52](晉)陳壽:《三國志卷二十八·魏書二十八·王毌丘諸葛鄧鐘傳第二十八》。
[53](晉)陳壽:《三國志·卷四·魏書四·三少帝紀第四》。
[54](晉)陳壽:《三國志·卷九·魏書九·諸夏侯曹傳第九》。
[55]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上)》1999年9月,文物出版社,第32頁。
[56](漢)班固:《漢書·刑法志》卷二十三刑法志第三。
© Copyright 2005-2021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版權所有